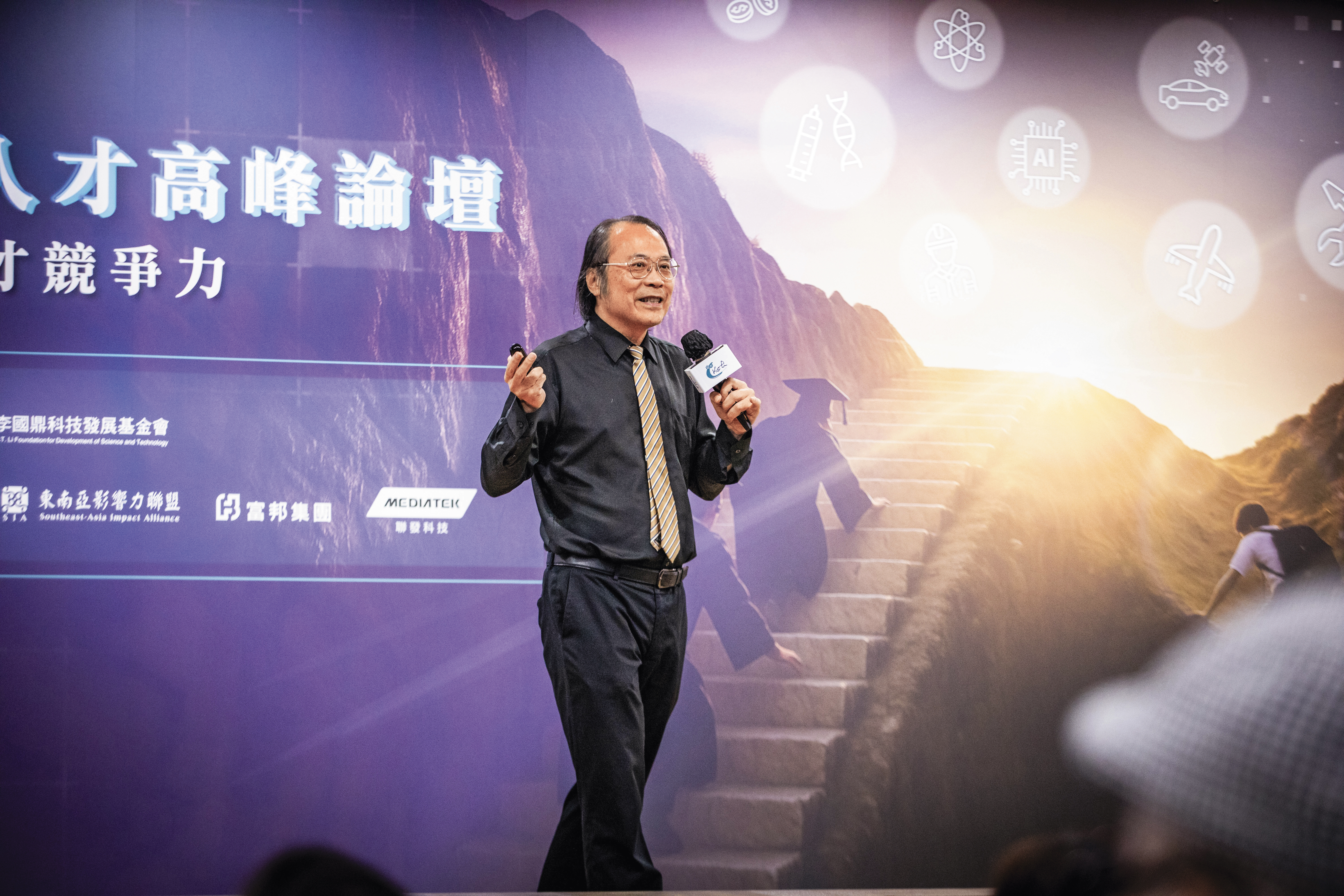簡立峰家的晚餐時刻常見火花,近年熱點是人工智慧,「我和老婆、小孩每天晚餐都在聊AI。」他在新書《台灣AI大未來》序言致謝家人,感謝資管博士太太與孩子們常來踢館,成為他的動力。從運算機制、科技倫理、投資策略到市場漲跌,這張餐桌更像一枚運轉中的創業加速器。
「我小孩都資工背景,老大論文寫大型語言模型(LLM),從事AI產品技術管理;老二論文寫台積電供應鏈使用AI相關計畫,內容敏感,目前還不能公開。」他2個孩子都在台灣長大,赴美學成又回台灣。他接受視訊訪談,背後白牆掛著孩子5歲的水墨畫,畫中是宜蘭老家。孩子們成長軌跡與專業養成相似,老大更酷愛人類學,「孩子給我更哲學層次的思考。我們從人類學觀點去討論未來的AI—它是真聰明?還是假聰明?它只是純粹記憶力非常好?或者,它也有能力去遺忘?」
從不社交的 董事總經理
62歲的簡立峰曾任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台大教授,最為人熟知的身分,是前Google台灣區分公司董事總經理。他退休後擔任台灣AI公司Appier沛星互動科技、iKala愛卡拉董事,同時是60多家新創顧問,名片上沒有任何抬頭,只有一行E-Mail。

他自Google退休後,整天抱電腦宅在家,平均每日行事曆塞6至8個線上行程,一場視訊會議結束,無縫接軌下一場。接受視訊訪談這天,中午他與金控老闆開會,下午視訊處理媒體專欄,緊接著接受我們訪談,結束後還有下場視訊行程。9月25日下午,他自外縣市趕回台北,出席2025李國鼎基金會主辦的高峰論壇,他全程不看稿,講座結束,眾人湧上交流,他傾聽各方邀請與提問,最後不好意思地說,時間真的有限,稍晚還要趕場,「我今天(忙到)還沒吃東西,我到傍晚都會發抖…」
「我沒出國念過書,但在台灣,書念得最好的人,都未必找得到我這麼好的工作。不出門就能做天下事,那留在家最好。」簡立峰退休後常待在宜蘭老家照顧父母,夜裡僻靜,幾無光害,只剩滿天星。他下班不應酬、上班不社交,LINE聯絡人是個位數,「我喜歡幫人解決問題,但不喜歡social、沒有註冊任何social media。」「我從小到大都不social,那會花掉很多時間,還不能做自己。而且,social的場合,可以幫助人的地方非常有限。」
他一直覺得宜蘭之於台北,如同台北之於全球,看似邊陲,其實接近核心,「就好像你身處十字路口旁小巷,走幾步就到十字路口,可往回幾步,又退回巷裡。」「無論發生什麼事,我心情都不大會受影響。我和全世界的人視訊完,可以立刻回到我的安靜小巷。」
對大多台灣企業而言,視訊工作型態是疫後普及的協作方式,卻是簡立峰的日常。1/5世紀前,簡立峰身為Google台灣員編第一號,身旁沒有台灣人—更精確來說,他身旁沒有人。

「早在2006年,我就一人加入Google在台北101的辦公室,第一年做全球計畫,所有人都不在我身邊,我在Google完成十幾個研究計畫。」他笑咪咪說,「我每天腦袋跟美國同步,已經快30年,團隊遍布全球,我穿拖鞋在溫州街走路,下通視訊來自印度,再下通是MIT(麻省理工學院),下下通是Stanford(史丹佛)。」
「我們家族好幾個小孩在矽谷,員工挫折感非常大,表現再好都沒用。現實很殘酷,科技公司就是裁員、裁員、裁員。」簡立峰家族多人任職全球知名科技廠,甚至有人負責開發3D IC設計核心演算法,「矽谷現在非常捲(競爭激烈),裁撤量高得驚人。因為企業覺得,要把握AI發展機會,趁機騰籠換鳥。他們相信,激烈競爭,會刺激員工更懂得AI。」
冒牌者症候群 三度發作
世人眼中的超級勝利組,其實一直知道何謂殘酷。簡立峰常受訪暢聊產業、管理、科技與地緣政治,卻幾乎不聊自己。曾有主持人問及他人生挫折,他只淡淡一提:大學聯考滑鐵盧。
聯考前,簡立峰模擬考成績一直排在宜蘭縣前30名,「聯考成績出來,我真是嚇到,比預期分數低太多太多。我一直在尋找,到底哪裡出問題?大學4年,我花了好多時間探索自己。」
以為會上台大,卻分發上淡江大學電子計算機系,他大多時間泡在淡大圖書館,想找出答案。有老師曾問他:「這好比你跑100公尺,為什麼一開始跑很快,卻在90公尺時自我減速?」他自行找出解法,「從那之後,我的目標就不再是100公尺,而是120公尺—從此再也不失常。」

大學畢業,他考上台大資工所碩、博士班,1991年發表的博士論文主題,就是語言模型(language model),成為台灣第一位研究語言模型的博士。台大博士班剛畢業,他發展出中文檢索技術,技術移轉廠商後,開發出如今研究生與學者都在用的「全國博碩士論文線上檢索查詢系統」;他從念碩士就在補習班教書,台下全是想報考資工所的大學生。
「但這些對當時的我來講,都不夠。讀台大那6年,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冒牌者,我的老師只收台大前3名畢業的學生,我是例外。」「老師很信賴我,可是,我不信賴我自己。」那6年,簡立峰每天苦讀,衣服只穿黑色,連吃6年校內賣的「小福(台大小福利社)便當」,只因他覺得思考吃穿都浪費時間,「我沒比別人聰明,只能比別人認真。」
博士班畢業後,他許多同學任教大學,他卻去中研院當研究員,「當我拿到博士學位時,自己並沒有承認自己的學位,我仍有冒牌者心態,覺得我還差別人很遠啦。所以,我選擇去當中研院研究員,等於是當一個『永遠的博士班學生』。」
從博士班到服務中研院,簡立峰專注研究語言模型與搜尋引擎,研究主題曾被同事說「你的領域很冷門」,如今已成為全球最紅的科技顯學。「當時在充滿外國博士的中研院(系統),我覺得他們不信任我這本土博士,而且,我還是私立大學畢業的…那種冒牌者感覺,又出現了。」
2006年,43歲的簡立峰加入台灣Google,「我是全球高階主管,卻不曾出國念書,英文也不好。冒牌者感覺又來了。」他又笑咪咪分析,「我在台大、中研院、Google,人生三階段都是冒牌者(身分)進去的。但出來的時候,好像…都還不錯。」
「我的同理心,就是這樣來的。某種程度,我是個geek(美國俚語,指智力超群,擅長鑽研但不愛社交的知識分子),但為什麼溝通能力還算不錯?因為我一直習慣換位思考—那些最優秀的人,通常不需要換位思考,他們不會知道困難點在哪裡。當有一天,你天賦沒別人高、永遠都覺得自己是個冒牌者,你就知道人們的困境了。」
形容詞對我來說 很多餘
同理心讓他透析他人困境,演算法般的思考模式讓他總能照見問題核心。他往往不用看資料,就能旁徵博引最新報告、資訊、數字,還附資料來源。他兒時讀書就發現自己不喜歡形容詞,「形容詞對我來說是多餘的。我不感性,也不人文。」「給我數據就好。我要事實。」
他長年和全球菁英(其中也有大量geek)打交道,例如早期台灣數學奧林匹亞競賽金銀銅牌,大概有2/3曾任職Google;「你對這些人完全不能設限、不能懷疑、不能說他沒紀律。你只能鼓勵他們。」「我的鼓勵方式喔?就是交給他們超人般的任務…」他自己答完,哈哈笑到微岔氣。
在Google上班時,簡立峰對助理第一條規定是「不可幫我訂便當」,只因他認為人人平等;退休後任何邀約,若他答應出席,往往拒掉所有排場與宴飲,騎Ubike往返會場。負責採訪整理《台灣AI大未來》的作者蕭玉品觀察,簡立峰和全球頂尖專家共事多年,卻完全沒架子,且高度自律,「他一天好幾場視訊、一年百場實體演講,每天抽空運動、每週回家照顧爸媽,全部自己安排聯繫,沒有祕書、助理。」
任何人成功 都與我無關
2020年,57歲的簡立峰婉拒美國總部多次慰留,正式從Google退休。沒有社交活動的簡立峰採「全被動式」接受外界邀約,如同既往,全部行程透過E-Mail聯繫,他至今幾次受訪和出席公共場合,都穿黑色衣服,「這樣我就不用傷腦筋找任何衣服,我專注的一小時,可以幫總統、上市公司老闆,也可以幫年輕小朋友解決問題,我要高效運用時間,別把時間浪費在我個人身上。」「任何人的成功,都和我沒有關係。我在乎的是:我那一小時給別人的時間,有沒有盡全力?」
2020年,Youtuber、簡訊設計共同創辦人張志祺加入AAMA台北搖籃計畫,成為簡立峰的導生。張志祺回憶,疫情解封後2人第一次實體見面吃飯,全程都在聊AI,此後每次2人吃完飯,簡立峰離場時幾乎都騎著Ubike,奔赴下個行程。
張志祺自稱本來也是個宅男,只想在自己領域過舒服人生;去年底推出AI打造的數位分身,關鍵因素之一,就是簡立峰持續分享趨勢、不斷鼓勵。「老師說,他不想今天、不想明天,永遠在想『後天的事』;因為今天、明天的事,會讓大家競爭吵架,但思考後天的事,你不會有敵人,而且在未來,大家都可能成為你的夥伴。」
例如,早在今年初,簡立峰就告訴張志祺,AirPods Pro 3很可能推出即時翻譯功能。不久後,蘋果公司果然宣布:AirPods Pro 3將Apple Intelligence即時翻譯功能置入耳機。張志祺回憶:「老師今年初就告訴我:你要知道—語言的東西即將被打開了!可以為這件事先做準備。」
「我覺得,那麼多人尊敬他(簡立峰)、大家都叫他老師,是很有道理的,他真的很願意分享。我常覺得我何德何能、我是什麼咖?可以三不五時寄信給他,然後占據他一、二小時?」AAMA導師導生制度效期一年,但張志祺至今仍常寫信請教簡立峰,「老師每次聽完我的問題,都會很認真幫我分析:這次要注意什麼?可能有什麼風險?還有,永遠記得:要替人雪中送炭。」
大腦開外掛 別輕易外包
AI年代,簡立峰常提醒一個概念:別把大腦外包給AI。
「『大腦外包』是AI對每個人最大的打擊。」他解釋,許多人認為有AI就無須學習,「這跟你用Google Maps導航很像。你依靠導航久了,連隔壁怎麼去都不會了,但你可能因使用導航,到達從沒去過的地方。」「這是種交換。我們換一點、換一點,可能得到很多;但一不小心,就交換過了頭。我們熟悉的東西,會因此變得不熟悉,可是科技解決我們原來解決不了的問題。」說到底,我們交換出了什麼呢?「不知道。」他難得給出不確定的答案。
「大腦外包久了,你就不學習,久而久之,喪失所有基本能力。」簡立峰演講時很愛放一張PPT,畫面有點驚悚:西元250年前後,巴黎主教聖德尼遭迫害殉道,遭利劍斷頭後,仍撿起地上頭顱,捧著斷掉的頭,繼續講。「古代哲人死了都要把頭捧在手上;但現代人某種程度上,有了AI,我們自己把頭(思考能力)交出去。」

與「外包大腦」相對的另一種可能是:「外掛大腦」—他解釋,這好比把AI當成瀏覽器,如同日常透過瀏覽器吸收知識與資訊的過程,瀏覽器不僅記錄使用者的瀏覽內容,更深刻了解使用者的喜好與習慣,若善於利用,累積的數據更全面。
「如果可外掛大腦,把這拿來當成你個人資料庫,這不是很好嗎?對AI來講,它了解你,一個外掛大腦可以為使用者做很多個人化服務。」他又想出一個頗具生活感的比喻:「我們和爸媽講話,是不是都比較直接、比較凶?因為爸媽懂我們嘛。而那個『懂我們』,其實就類似AI的『無形服務』,也可視為一種瀏覽器。」
科技從未脫離人性,所有進展最終仍回應人類基本需求。簡立峰母親畢業於日治時期的蘭陽女中,近來他讓母親與手機AI對話,搜尋高中時代的老校舍照片。老人家嚇到直呼:「這AI感若(好像)神仙咧!」他覺得,AI好像給老人開了記憶外掛。
他父親高齡97歲,日前住院苦等不到醫師,他擔心老人家看病科別多、治療角度不同、藥物副作恐互相矛盾,又開起外掛,將父親年齡、症狀、病程與藥單發給Gemini,結果發現某顆藥不適合父親長期服用,Gemini建議可減一顆藥,後來主治醫師也確認可行。科技意外成了第一線的依靠。
人生的感性 都給了家人
自稱「不感性也不人文」的簡立峰,人生裡的最感性,其實全都給了家人。簡立峰讀台大博士班時,在台大資訊中心教書打工,認識大學部的學妹,苦苦追求。學妹後來赴美深造,簡立峰一天寫一信,2年後學妹學成歸國,「我寫了500多封信,她就回來了。帶著行李和一箱的信。」「還好有追到她,否則她就不回來啦。她為我犧牲滿大的。因為那時,留在美國發展比較好。」
學妹卜小蝶後來成為師大圖資所所長、教育學院副院長,現已退休。張志祺說,簡立峰有浪漫一面,例如導生們幾乎都知道,任職Google前,簡立峰曾拿到微軟中國的聘書,然而當他告知太太,她眼淚馬上掉下來。簡立峰立刻回絕微軟,放棄超高薪邀約。簡立峰夫婦對話也總不離最新科技;他曾在許多場合分享老婆的旅行趣事,「我老婆出去玩,在芝加哥走路走到腳破皮,去藥妝店買繃帶,幾十種不知怎麼選。她拿手機一拍,讓AI幫她選。AI還把使用說明都告訴她。」
當人工智慧快速滲入各行各業,焦慮成了普遍情緒。許多人擔心,自己的角色是否終將被演算法取代?佛教團體法鼓山也邀簡立峰演講,法師們給他出了一道題:聖嚴法師的著作體系清晰、資料充足,AI在語言回應上幾近無懈,宗教會被取代嗎?
簡立峰坦言對宗教並不熟悉,便請AI協助分析,從全球宗教到佛教,再談到聖嚴。透過與AI對話,他發現宗教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類無法完全參透生死;「臨終時,沒人希望陪在身邊的是機器、是冰冷的AI。人們渴望的,是那個對自己有意義的人,握住自己的手。」於是他對法師與信眾說:「分析到這裡,就釋懷了。就把AI當成新的傳播媒介吧。」
法師們的這一問,其實點出AI尚未能碰觸的核心問題—人類的精神與情感需求是否能被取代?人類該如何與AI對話,才能理解它的邊界、守住「生而為人」的位置?
簡立峰說,台灣人才解題能力超強,但普遍欠缺提問能力。他任職台灣Google時,曾聘用一千名同事,其中有900多名工程師,卻連一位來自台灣的產品經理都沒有,「這反映出台灣教育模式習慣讓學生回答問題,而非鼓勵學生思考:『我如何問一個好問題?』」
「學歷這件事,在台灣影響大,我們用考試去把全社會排名,這超病態,像工業時代的工廠,因為這套系統最方便管理人。」簡立峰直言,教育確實讓台灣成為製造業強國—台灣小孩老是習慣在既定規則裡找答案,培養出的人才服從紀律、擅長解題,卻很少有人被鼓勵去出題,「但到了AI時代呢?我們要出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