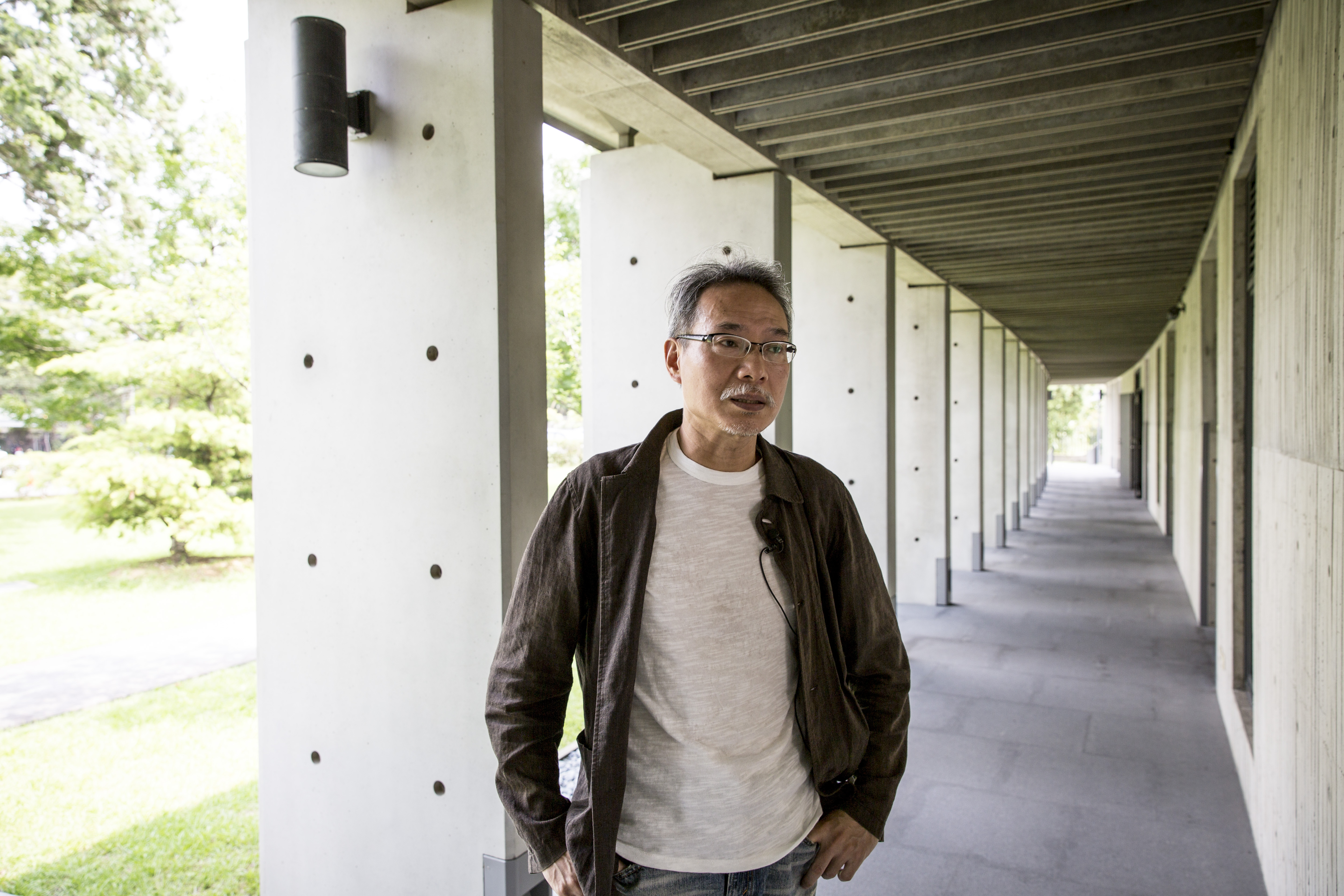倒是想起了初訪時問過他,為什麼大學志願全填建築系?他的回答是:「我們那年代對建築系的認知,就是『圖畫得不錯,那就進建築系。』反而不會有人叫你去讀藝術系。就因為這樣,我認定非建築系不可,根本搞不清楚建築系是怎麼回事,就進去了。」
但真的讀了,也不覺得和想像有太大落差,「我覺得真正的落差,比較在出社會、真的進入這個行業後。我們那時還好一點,很多人還沒有家屋,所以對建築系而言,那個使命感還蠻正確,出去就是要設計家屋,設計各式各樣的住宅給人使用,設計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設計一個可以安居,可以安心的地方。」
他心中對「建築」一事的核心標準,就是如此而已。雖自稱是「人類滅絕主義者」,但聽過上述發言,就會發現他其實心口不一:他終究把「人」放在「地球」之上,為了「人」,他可以把建築的位置擺高,甚至也不再那麼心虛。
但現今的建築狀況,已經和他當學生時完全不同。在建築系教書的日子,他清楚感受到從前就存在的「學院」和「現實」落差,早已擴大到斷崖程度。「我們進大學時想都沒想到,人類對這個地方的開發,可以在短短幾十年內改變這麼多,空屋率這麼高,此時再去談我們建築系就是要設計讓每個人都有地方住,已經不合時宜了。當這個量過剩到這個程度,房子就不是拿來住,而是拿來投資的。所以有段時間我們看那些產品,都覺得是長得像房子的股票。」

小小的懷疑的火苗出現,很快就野火燎原。他逐漸減少業務,終至歇業。學院裡的課程,也全部停掉。
他要讓自己講話理直氣壯,不落人話柄。他說:「友直,友諒,友多聞,至少我有做到『直』這一項。」
但還是不宜如此回答代女兒問問題的人吧?他輕描淡寫說:「建築跟畫圖,不見得有絕對關係,這裡面有太多東西不是由繪畫決定,所以要我給意見,恐怕給不出什麼意見……就先走一段路吧,走到能提出問題了,就會知道了。」
他真的很重視「問問題」這件事,好像「問題」已經擺在那,就等人來問。我說:「老師好像對學院沒有太大的信心?」他不直回答,只說:「建築系是很容易讓人沮喪的地方。」那沮喪,同樣是落差所致。如果沒有過期望,沒有過理想,怎麼會沮喪?
他舉例說明:「有一年我去台大社會學系演講,題目叫『從建築看社會』。我講了一些從建築角度看到的社會議題,學生聽完後很有興趣,我就問了:『我一進系上,就看到一堆公告,各式各樣訊息,什麼社會運動需要你的參與……請問,有哪些是你本來就在意的議題,還是受到系上的氛圍所影響呢?』結果沒人回答得出來。」
在已有的選項裡找答案,真的算是獨立思考嗎?他問台大學生的問題,自己的答案又是什麼?他說:「我也答不出來。」外加一個妙喻:「會不會擺在你面前的這些糖果一到糖果十,都是被選定的,你沒有糖果十一的選擇。對我而言,我就是一個努力想找出糖果十一的人。」
曾有學生會問他:「怎樣才能設計出得獎作品?」他聽後覺得這問題也「太好玩」,因為怎麼可能有答案呢?「像在夜裡直視一顆星星,你愈用力看,愈可能看不清楚。反而用眼角餘光去瞄,能看出端倪。」說得十分之玄,我卻覺得那個用眼光餘光瞄的地方,可能就是放著糖果十一的地方。
因為一直往外瞄,他於是離建築愈來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