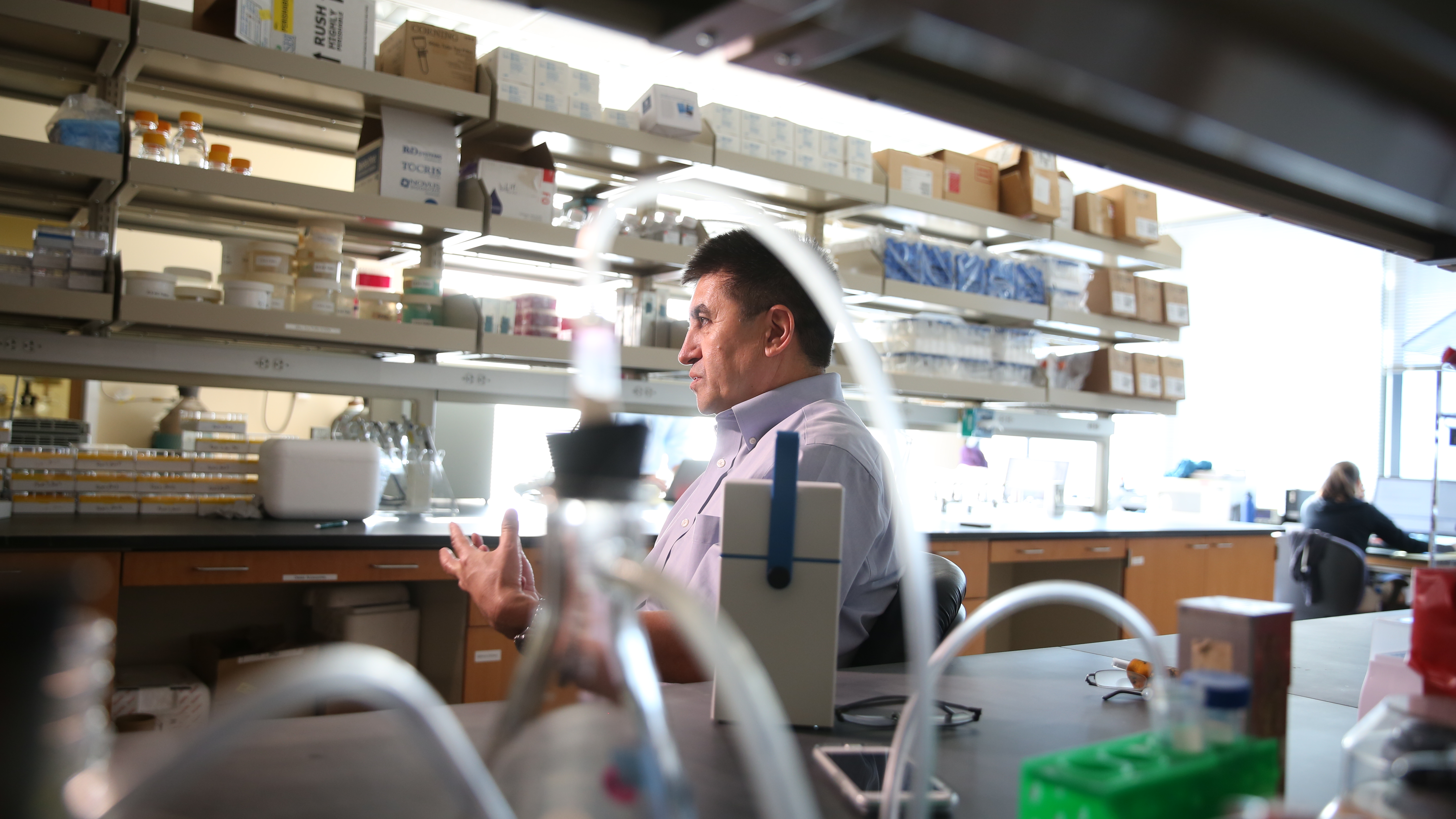問:CRISPR這種基因編輯工具非常容易上手,操作也容易,你們的方法和別的實驗團隊有何不同,以至於有此破天荒的成果?
答:我們的目標有點不同。胚胎的每個基因都有兩股DNA,其他科學家都把目標鎖定兩股,這表示他們會把兩股都剪除。
我們則不一樣,我們只有一股突變,另一股是正常的。變異的基因來自精子,卵子則提供正常那股,我們設計的CRISPR只針對變異的基因,因此不會剪除另一股,這是我們的設計有些不同之處,我猜,當另一股沒被剪斷,沒有被CRISPR破壞時,那個基因就讓自己變成模板,充當修復的藍本。我們也是這樣才發現了胚胎自我修復非常獨特的能力。
我們的發現,之前的研究人員都錯過了,因為他們兩股都剪掉了,當你兩股都加以破壞,就沒有修復的藍本。
過去我們不知道,基因內沒被剪斷的那股會被預設作為修復的藍本,我們相信這可能是非常常見的機制,目前我們只在胚胎內看到這情況,我們認為或許早期的胚胎是以這種方式,但也有一些案例顯示,其他細胞也有類似狀況,因此關於我們的這些發現,還有太多疑問。
以前沒發現過這情況,因為過去我們沒有CRISPR這種工具,如今我們可以測試許多生物機制,結果在我們的胚胎研究結果中看到了這樣的狀況,這證明我們還有太多生物學不瞭解,我們以為我們了解細胞如何修復基因、修復斷裂的基因,但顯然它們的機制和我們以前想像的不同。
問:這項研究的發現意味著什麼?人類距離可以把致病基因刪除越來越近了?
答:我們確實往前跨了一大步。我總是強調,我們做這些人類胚胎的研究,不只是為了瞭解基礎生物學,了解基因如何修復,主要更是著眼於未來可望運用在臨床上,我們相信這一天會到來,我不確定多快,或許五年,或許十年,這項技術將可用在臨床,第一個基因修復案例將出現,希望我們在論文中做出的發現,有助於更快地推動進展。
我認為所有疾病都必須獲得治療,在醫學史上我們治療了許多種類的疾病,無論是感染性或癌症,我認為基因疾病有點不同,因為我們必須用基因工具來治療,我認為那一天會來到,屆時我們將學會如何矯正變異基因,使父母不會遺傳給子女。

問:對於這類研究,最感到興奮的可能是家中有罹患了基因疾病成員的人?
答:我們和他們保持聯繫,許多家庭主動想參與臨床實驗,他們提供樣本,我們也因而設計了許多研究,因為我們的樣本來自真正的病患。
比如說這項研究就是一位帶有肥厚型心肌症的男性病患,他自己知道帶有這種突變基因,我們向他解釋這項研究的用意,他非常樂意參與。
問:印象中有哪些特別難忘的病例嗎?
答:當然,這些家庭都很悲傷,他們知道自己患有疾病,無論是自己還是孩子,當然他們愛自己的孩子,但他們的想法是,希望其他人以及他們可能孕育的下一個孩子,不要再承受同樣的磨難,這些故事讓我們很感動,也因此,即使我們因為進行胚胎研究而面對爭議,飽受批評,還能維持堅強。我們繼續推進,因為我們知道到頭來,未來將出現革命性療法。
問:研究結果曝光後,再次引發設計寶寶的疑慮,您認為這種反應有些過頭了嗎?畢竟人類還不知道控制髮色、智力或運動細胞的基因是哪些?
答:正是如此,可能控制這些表現的基因有好幾百個,除了基因,可能有些別的因素也很重要,尤其是智力,後天父母的教養,可能也會影響孩子。我們還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個基因可能造成影響,以及是如何影響,因此我認為這樣的反應有點過度了,我們想治療的是疾病,尤其是會在孩子身上引發特定狀況的基因突變。我們不該只因為擔心可能被用於其他目的,就索性全面禁止。
再說到對經費的限制,研究總是十分昂貴,多數情況下我們仰賴聯邦政府的資金,通常NIH是我們主要的經費來源,但根據現行法規,我們有關人類胚胎的研究不能用聯邦的資金,這當然嚴重阻礙了這個領域的進展,也因此很少有實驗室在進行這類計畫。
問:那經費的來源是?
答:因為政府不支持這類(涉及人類胚胎基因編輯)研究,我們是透過一個基金會募款,也接受慈善機構的捐助。
問:您關於剔除變異基因的研究,是與韓國、中國以及沙克生物研究所(Salk Institute)聯手合作,部分原因是受限於經費?
答:是的,有時候我們一起分擔費用,由於政府的限制,我們無法自己承擔這麼多。這間實驗室主要是為了臨床研究而設的,所有的器材都是校方(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OHSU)購買的,但我們另外有小鼠和猴子的研究計畫,這些就有得到政府的支持。
所以,政府對於支持動物研究毫無芥蒂,卻不支持人類的研究。
問:您是不是覺得這有些諷刺?
答:我猜也別無他法,當然,國家衛生研究院(NIH)了解這是重要的研究工作,我們之所以進行猴子實驗,正是為了驗證是否安全,未來才能用於臨床。但囿於法規限制,即使他們有意願,仍無法直接提供我們經費,但這不是NIH的政策,是國會設立了資金的相關限制。

問:但根據現在的法規,修復了基因的胚胎無法植入母體,無法證實究竟有沒有效?
答:沒錯,(修復了變異基因的)胚胎只被允許存活幾天,當然我們無法確切得知寶寶會一切安好,這部分還有待未來。我們可以做很多動物實驗,小鼠當然還有猴子,我們製造猴子,進行研究直到牠們成年,我們也繁殖猴子,不過你說的沒錯,還是必須在人身上試驗。
問:您曾表示,研究結果比預期更好?
答:是很大的驚喜,因為有時胚胎會自我修復,但機率很低,而在最初的實驗中,我們就發現修復比例非常高,一開始就有50%的胚胎修復了,我們很驚訝胚胎自我修復能力這麼好,真的沒預料到效能這麼高,這也是我們必須多次重覆的原因。
為了這項研究我們用了160多個胚胎,精子捐贈者只有一個,卵子則來自12位捐贈者,因為我們要證實(修復變異基因)不只發生一次,而是12次,因此我們很篤定,我們的胚胎修復機率很高。
問:但如今有一群科學家質疑您的研究成果?
答:這項發現的影響巨大,而且在科學界質疑研究成果是很正常的。他們質疑的是修復是怎麼發生的,由另一股正常的基因作為模板,這算是項新發現。
通常這類發現必須透過不同的突變基因再次驗證。我們必須等待重新驗證的結果出爐,屆時我們就會理解,這不是單一偶發事件,而是先天就是如此。希望我們發現的這種機制,對於其他的變異也會有同樣的功效。
如果真是如此,隱含的意義不只是胚胎基因修復,或許也可用在癌症基因修復,我們相信這可能是基礎生物學的一部份。
一生中基因會因為損害而突變,通常這是隨機的過程,通常只有一股會被破壞,我們的想法是,第二股總是存在,提供修復的藍本,基因修復必須尋找一個藍本,這是DNA重新修復的方法,必須依照某個已經存在的片段,看來第二股扮演的正是這個角色。我們在這些胚胎研究的發現提供了證明,顯示這是自我修復的常見機制。
問:目前下一步計畫是?
答:通常有重大發現時,我們必須用不同的基因複製同樣的實驗,加以驗證,我們現在已開始進行。
我們的研究中只有一股有突變,但有些疾病是兩股都突變,這該如何修復?我們必須找出方法,來矯正這些突變。

問:您曾幾度創下第一的紀錄,有人把您喻為科學狂人?
答:這是我們專精的領域,早期胚胎發展,這是我們做的事。我是個胚胎學家和基因學家,當然我們做的所有事都像是嶄新的,但我們試圖把工作做得非常好。如果你被允許做人類胚胎研究,就必須是考慮非常週詳的計畫,可以回答一些大哉問,因此我們的每一個計畫都試圖回答很重大的問題,確保這些大計畫值得。
問:您對胚胎學和基因學這麼感興趣的原因是?
答:這是我擅長的領域,已經有好幾百萬個孩子透過體外人工受孕(試管嬰兒,IVF)出生了,科學一直往前推進,我們希望以體外人工受孕為基礎,開發新的平台,其中一個新平台就是遺傳疾病的基因療法。我們在這個領域已努力了近十年,也感到很榮耀,在基因治療領域做出了重大貢獻。
我們在細胞核轉殖、複製、粒線體移植等方面都做了很好的研究,如今則是基因療法,這都是計畫的一部分,我們需要設定研發出生殖系基因療法的目標。
但生殖系基因療法是非常具爭議性的領域,主要是因為安全性和有效性,但我們相信安全性和有效性可以改善到或許可以放行臨床試驗。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要確認,研究科學不只為了追求科學的進展,當然很多基礎科學可以完成,但在基礎生物學和治療之間,如何拉近彼此的距離,許多科學無法有太多進展,因為臨床科學進展太有限。
問:發現基因編輯工具的Jennifer Doudna曾呼籲全球暫停使用CRISPR來改造人類基因密碼,您的看法?
答:他們呼籲暫停的是,不要立即把胚胎用於母體,我想他們都認為這類研究必須繼續,否則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這個程序到底有沒有效。
CRISPR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為基因的修復不是靠CRISPR,而是自我修復,這也是我們不瞭解的部分,因此這些研究必須繼續,或許是動物模型,以及人類胚胎。人類胚胎我們只能在前幾天做研究,當然我同意,目前還有太多東西我們不清楚,也還沒有準備好加以運用,就算真的進入臨床,也必須在非常嚴格的監視下進行,我認為不能讓私人IVF診所自行注射CRISPR,必須是像我們這類的學術型實驗室,已經知道它運作的方式,也知道要尋找什麼,以及如何做切片。
在目前,我同意臨床實驗實際尚未成熟。
問:《經濟學人》說,這項研究有贏得諾貝爾的潛力,您怎麼看?
答:這類發現必須經過許多許多年的驗證,短時間內我們應該不會被列入考慮,但我們做這些研究不是為了獲獎,而是用於臨床。確保新生兒的健康,比任何獎項更棒,這也是我們持續茁壯的原因,我們不希望研究成果無法用於臨床,我希望我退休時,這個計畫能用於臨床。若這項技術能讓孩子健康地誕生,對我來說是最值得寬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