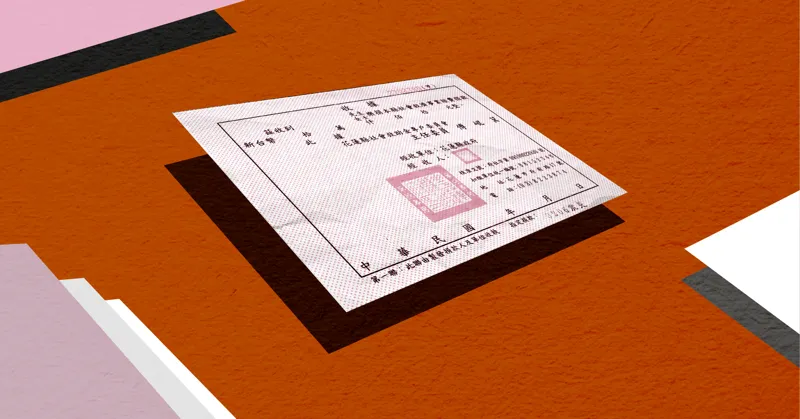「花蓮現在瀰漫著一種不安的情緒,大家都很低迷。」花蓮縣無黨籍議員楊華美分享 403 大地震後目前災區的情況,「短期的安置已經結束了。一開始在中華國小安置⋯⋯後來大家就各憑本事,自己找關係、找地方居住。但是未來呢?」
花蓮縣長徐榛蔚於 4 月 21 日的記者會表示,此次的災損是 206 花蓮地震的 10 倍,有近 2000 戶受災戶;楊華美指出,「這次的災情比 206 廣度更大。待拆的房子有幾 10 棟、紅黃單數百件,都需要很大量的善款、跟很大的政策支持才可能解決。」
中央政府於災後一個月提出「0403 災後復原重建方案」,預計投入 285.5 億元(包括善款 16.45 億),從災民安置、災民建物及公共設施的補強重建、振興觀光、到產業融資紓困幾個面向幫助花蓮重新出發;花蓮縣府也募到 5.6 億的善款,加上之前地震的善款餘款,共有 8.7 億用來協助災民。
此次善款比 2018 花蓮地震少
此次花蓮縣政府募到 5.6 億的善款(截至 5 月 13 日),相較 206 地震善款短少,並不能直接代表民眾愛心的消逝,因為花蓮縣政府並不是此次地震唯一的募款管道,行政院責陳「賑災基金會」募款,獲得 16.4 億,兩者相加仍少於 206 地震募到的金額。

是什麼影響了民眾捐款的意願?花蓮縣府秘書饒忠於 4 月 16 日說明會上回應災民需求的發言引起爭議,現場有民眾直嗆「政府濫用善款才沒人捐錢」,饒忠回答:「你如果看 FB 就知道,很少人捐善款給我們,花蓮縣府現在可用資源真的很少」,被認為是在怪罪災民,事後他回應是「公部門預算不能用在私人建物上,要用善款支付」。
從地震發生以來,網路上出現許多「不要捐花蓮」的留言,綜整原因,一部分來自花蓮縣政府在上次地震的善款分配惹議、一部分來自於前花蓮縣長傅崐萁在地震後的爭議行為,例如他在臉書貼了「禮盒山」的照片,原本是想強調地震很大,下方卻出現許多留言批評他「收禮不清廉」;或是他在地震後前往中國交流,也遭批不顧災民。
雖然無法真正得知捐款人的意願受到什麼影響,但兩次地震,中央代表的賑災基金會、和地方專戶的收到的金額差距,某種程度顯示了捐款人的信任轉移。
災難善款新模式:政府募、財團法人分配
公益媒體「Right Plus 多多益善」創辦人葉靜倫提到,除非是衝動捐款,否則一般捐款人對捐款組織都有基本的認識,「但災難是突然發生,在這麼短暫的時間要叫捐款人去認識一個單位,捐款時就會有『信任應該要寄託在哪裡』的問題。」
過去的三個階段,無論主導的是民間團體、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善款的「募」和「用」都放在同一個單位(自己募自己花),「現在『募』和『用』分開了。這次由中央政府出來號召捐款,由賑災基金會來分配使用。中央政府某種程度保證了募款的正當性和資訊的真實性;而賑災基金會是全國性的財團法人,受到《財團法人法》嚴格監管,好像也補足了使用管理上的信任。」她提到。
她提供幾個觀察:首先,賑災基金會此次分配善款的方式,包括請各地方社會局處自行造冊(確認誰是災民、受災程度等),等於是由縣市政府各單位來確認災民需求;同時開放地方團體申請善款,可能可以補足全國性基金會不夠了解地方的問題。
第三,賑災基金會也正視了「善款使用名目」的爭議,它明訂若是政府公務預算足以支應,就不會用善款支付,但可以提供周轉金。
葉靜倫認為,「403 地震是再一次的信任轉移與寄託,我們開啟了第四階段的國家重大災難募款模式,我覺得它可能會成為重要的開端。」
而過去災難善款遇到的困境,可以寄託於這個新模式嗎?
困境一:善款如何真正幫助到災民?
由政府主導的善款分配,通常會設立「善款管理監督委員會」,其中政府官員的比例不能過半,也需要有災民代表,確保災民需求能被傳達。但葉靜倫直言,監督委員會是民主制度下大家想出來比較好的方式,跟「知道災民需要什麼」是兩件事。
資歷超過 10 年、參與過至少 5 個大型突發災難的政府資深社工 mounter 表示,災民的需求往往難以被充分反映,除了「傷亡者」的需求最容易被看見,「其餘的就只能靠有話語權的人協助發聲了。」
mounter 提到,通常是議題或事件出現之後,當事人透過民意代表、媒體、有特殊身分或話語權的民眾出來反映,地方政府在接獲訊息後,由業務負責局處先想辦法依現行措施研擬解決,但如果是新增議題或是既有規定措施所不能解決的,則再提到善款管理會中討論,並以專案計畫的方式申請賑濟補助方案。
「但這是權責單位『有將它當一回事』,並據以回應及解決的模式;如果當事人反映的問題不夠明確、表達能力不夠好、對口承辦人員沒有接續發聲、權責單位沒有深入追究事件的影響範圍及後繼效應,那這個反映事件,就很有可能淪為上千封陳情信中的其中一件存查案,而埋藏在檔案庫底之中。」mounter 說。

楊華美就提出實務上會遺漏的細節。像市府發放 1 萬元慰問金後,議員服務處馬上接獲民眾陳情,來自房東、房客都有,提及「慰問金被屋主(房客)領走」,「我立刻跟社會處溝通,因為金額不大,全發比較好,畢竟災難才剛發生,他們需要應急去買生活用品。」最後政府放寬無論有無設籍都可以領取,避免災民在有限的資源分配還需要針鋒相對。
「很多人覺得你沒有住在倒塌的房子裡,代表你有地方住,不需要補助,但實際上的樣態真的很多。」楊華美提到,有年輕人在花蓮買房,但因為就業機會太少,選擇把花蓮的房子出租,拿租金收入去臺北租房。若地震後只有補償房客,他拿不到補償、房子也租不了人,還要繳原本的房貸、臺北的租金,損失很大,「如果只是要防投資客,20、30 戶的包租公,可以用其他制度設計的方式排除,就是要多討論。」
而掌握主要善款的賑災基金會身為全國性組織,又更難掌握地方需求。葉靜倫提到,「賑災基金會本身沒有在做直接服務。不像其他全國性的基金會,例如伊甸基金會、世界展望會等,他們在很多地方都有據點,長期深耕在地服務,需要直接面對個案。但賑災基金會是中介組織,我們當然需要這樣的組織,但災民的需求調查和理解,應該沒辦法寄託在他們身上。」
因此賑災基金會如何處理「民間團體提案」的善款申請,值得關注。過去在地方政府主導的善款分配中,一向都是由各局處提案,這次在新的模式下既然納入民間團體的提案,值得期待。
葉靜倫提到,災害的影響大至房子倒塌、小至一個社區沒有水,「單一社區或大樓停水,對居民來說是切身的痛楚,因為他無水可用,卻細小到就連地方政府都不太可能掌握。」開放地方團體甚至社區管委會申請,有機會更直接理解災民的需求,但能細緻、深入到哪種程度?還是要看實際運作的結果。
「我也會關心它會怎麼去審核這些計畫、標準是什麼?以及它對這些團體的要求有哪些?能不能為像我這樣關心善款運用的人設立一些指標?例如,要求每一個團體定期更新計畫進度、提供洽詢窗口、說明計畫的重大變動等。都值得觀察。」葉靜倫說。
陳文良也提到,震災基金會讓民間團體來提案是一個好的方向,災後的重建不是只有政府的角色。此次震後重創國家公園,依賴觀光的東部民生必定要重新盤點,當地的商會、觀光業共同組織、甚至文史團體,有沒有機會受到賑災基金會的支持參與重建,民間的參與能不能夠公開透明,花蓮的在地組織、公益團體怎麼合作,怎麼為重建協調、找到共識⋯⋯這些面向值得後續追蹤。
困境二:誰來監督善款使用?
現行機制下,政府善款的使用要經過「善款管理監督委員會」同意,政府也會將委員會名單、會議記錄公開,以昭公信。但過往的爭議中,仍出現很多善款使用是否合宜的批評。
mounter 提到,現行的捐款管理委員會並沒有具體的法令去規範委員來源、組成人數比例等,多數是災害事件發生後,由地方政府訂定「行政規則」再據以執行。所以捐款管理會是讓地方政府展現出「管理責信」的工具,讓民眾能從制度上相信政府對於捐款的管理態度。
但他直言,「無論做什麼樣的救助政策,都可能因為五花八門的理由而被社會大眾所『討論』,那地方政府在組成捐款管理會的時候,當然會審慎考慮委員會成員,在事先的徵詢邀約上,即使不考慮政黨派系,也一定會優先選擇與地方政府較有默契的各種代表當作監督成員。這樣下來,即使未來不是每個提案都能無條件通過,但也不容易在重要決策或提案上砸自己的腳。」
楊華美也提到,善款金額這麼高,其實連議會都無法監督,只有委員會可以管。加上餘款轉移到重大災害民間賑災捐款專戶後,委員也沒有災民代表(註:不過縣府官員仍沒有過半,以花蓮縣來說,有一半是賑災相關之學者、專家及民間企業經營、管理專家),「對於各局處來說,就變成一塊很好用的資源,只要跟災害有關就可以申請,不用經過議會,只要說服委員會同意就好了。所以這次地震之後,我希望能提案訂定自治條例,讓議會至少可以事後備查。」
楊華美於 5 月 15 的縣政總質詢也提出幾個具體建議:由於監管委員的組成沒有民意基礎的代表,希望監管委員要有議會黨團代表;以及政府應主動到議會進行善款運用報告。
而此次賑災基金會雖然主責分配善款,但模式是由縣市政府、地方團體來申請,雖然賑災基金會仍會以委員會等機制進行審核,但想要進一步的監督也更困難。「這個模式是個雙面刃,或許不會再讓單一團體在其中被攻擊,但我們更不容易找到究責的對象、追蹤善款使用的流程。」葉靜倫說。
她舉例,地方社會局處負責災民造冊,而地方團體的管理則回歸《人民團體法》,由衛福部或其他主管機關監督,「等於把監督的單位分散了,責任其實也分散了。」

困境三:善款未設上限又用不完?
盤點過去災難善款的執行狀況,除了太魯閣號出軌案的捐款,是衛福部以「發完」為目標、100% 現金支付給家屬外,大多都剩下很多錢,例如高雄氣爆的餘款是捐款總數的 8%、206 花蓮地震剩餘 10%、臺南地震的餘款更是高達 34%。
葉靜倫認為,因為事態緊急缺乏規畫,事前未設募款上限,事後又被「專款專用」規範所束縛,導致結餘款動彈不得,造成愛心浪費,是災難捐款的痛點。
他舉例,2006 年梅嶺車禍委由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會設置專戶,車禍造成 20 多個孤兒,但他們評估孩子從小學到大學畢業生活費最高需要多少錢,設下 3 千萬的上限,不到一天就達標。「因為新聞太令人心碎,民眾無法捐款,還打電話進來罵。」
「設下上限,才不會像高雄氣爆一樣,即便後來政府放寬各種標準,依照各種(建物)受損、(民眾)受傷的情形把錢發出去,發得很徹底了,還剩下很多錢。但災民覺得善款就是捐給我的,為什麼政府不給我,造成很大衝突。」陳文良說。
他提到,梅嶺案能成功評估,是因為跟高雄社會局合作密切,可以精準評估社會救助,這仰賴經驗的累積和合作。
陳文良認為,應該賦予賑災基金會管理和彙整災難資料的功能,有豐富的資料,一方面可以作為研究的參考,對於災難的預測和重現也會更精準;提升到智慧國家的層次,如何為建構智慧化的災防系統,讓募款上限的依據來自多年災後重建經驗累積的資料庫,成為大數據,都很重要。
而此次賑災基金會為 403 花蓮地震募款,原本設下金額和日期兩種期限,希望在一個月內募到 10 億。4 月 15 日時已募到 9.5 億,當天基金會的新聞稿表示將會繼續募款至原訂 5 月 3 日期滿,因為「每多匯聚一份關懷,就能給災民多一分協助與支持」,最後比原目標多出了 6.4 億。

困境四:善款可以用在哪?
「善款可以用在哪、不應該用在哪」是過去幾次災難善款分配中,最容易出現爭議的點。從衛福部在太魯閣號出軌案被抗議後,改為 100% 現金分配來「符合捐款人期待」;到花蓮縣政府被認為濫用善款導致不再被信任,都可以看出輿論對於善款分配的影響力。
「但誰是災民?」Mouter 表示,「以 2023 年屏東縣明揚工廠大火、2015 年八仙塵爆、2021 年城中城火災案件為例,因為受災地點單純且有明顯的傷亡者,要界定災民很容易;但像高雄氣爆、莫拉克風災、臺南 206 維冠大樓地震倒塌、花蓮 206 地震等災害事件,民眾認同傷亡者是災民,但不見得認同相關產業跟週邊受影響的民眾是災民。」
當年 206 地震後花蓮縣政府曾評估運用善款協助縣內的石材業者,引發爭議,mounter 提到,「但石材業確實是花蓮的重要產業之一,它也維繫了許多家庭的生計,拿善款來協助產業復興,並不是件奇怪也不能做的事情,因為過往的災害事件也都有運用善款協助產業復興的先例:例如莫拉克風災後振助受創嚴重的南部山區觀光旅遊業,高雄氣爆事件後振助凱旋路上沿線的租車業。」
「民眾似乎並不是全然認同,先入為主的認為捐款只能用在災民身上。」mounter 憶起當年花蓮的爭議,「當年在一些網紅及自媒體的推波助攔下,引發了一波退捐款的行動,確實加深了捐款者與主政單位間的對立,但誰是災民?這是個很值得探討的問題。」
葉靜倫提到,重大災難時的緊急募款不太可能免除專款專用,否則首先就抵觸了民眾在此時最需要的信任感,「但有沒有可能去拓寬專款專用的邊界?例如消防局換設備,可能真的應該用公務預算,不應該由善款支應,但實務上我們也知道有些縣市就真的很窮,窮到消防裝備很匱乏,或買不起進階設備。」
她再舉例,「206 花蓮地震,其實他們後來修繕了很多東西,到後來也很難確定它是不是因為地震造成的。你可以說這面牆本來就要修,它用善款修是濫用;但換個角度講,它不修,地震確實就會有危險。很多用途都介於善款跟納稅錢的界線,很難區分清楚。」
再更進一步,如果只有災民可以拿到錢,那誰來幫助災民?陳文良提到,以前遇到捐款人說「我希望我的錢交到真正需要的人身上,不是用在你們的薪水上」,但沒有人力,救災無法完成。
mounter 以「寄送捐款收據的郵資」為例,臺南地震有 43 萬多筆捐款、高雄氣爆有近 29 萬筆捐款,以當年平信郵資每件 3.5 元的標準計算,光要寄送收據就得花 100 多萬元,是一個行政機關好幾年的預算加總,但這些錢要從哪裡來?但如果規劃從捐款做行政經費支出,又可能被質疑。
陳文良認為,善款使用的標準,「是社會進步的過程中,公益團體的公開透明去教育所有捐款人的過程,它永遠不會有標準答案。」
他會嘗試告訴捐款人,災難從解除緊急狀況、長期的拆後重建、到恢復正常生活,中間要歷經很長的過程,921 前後就經歷了 15 年。而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工作要做,公開透明定期告訴大家善款的用途。
雖然善款監督委員會的會議記錄、善款支出明細基本上都會公開上網,但陳文良認為政府應該更積極主動向民眾解釋,例如比照 COVID-19 疫情時定期開記者會、直播,來累積信任。
記者:李又如
設計:曾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