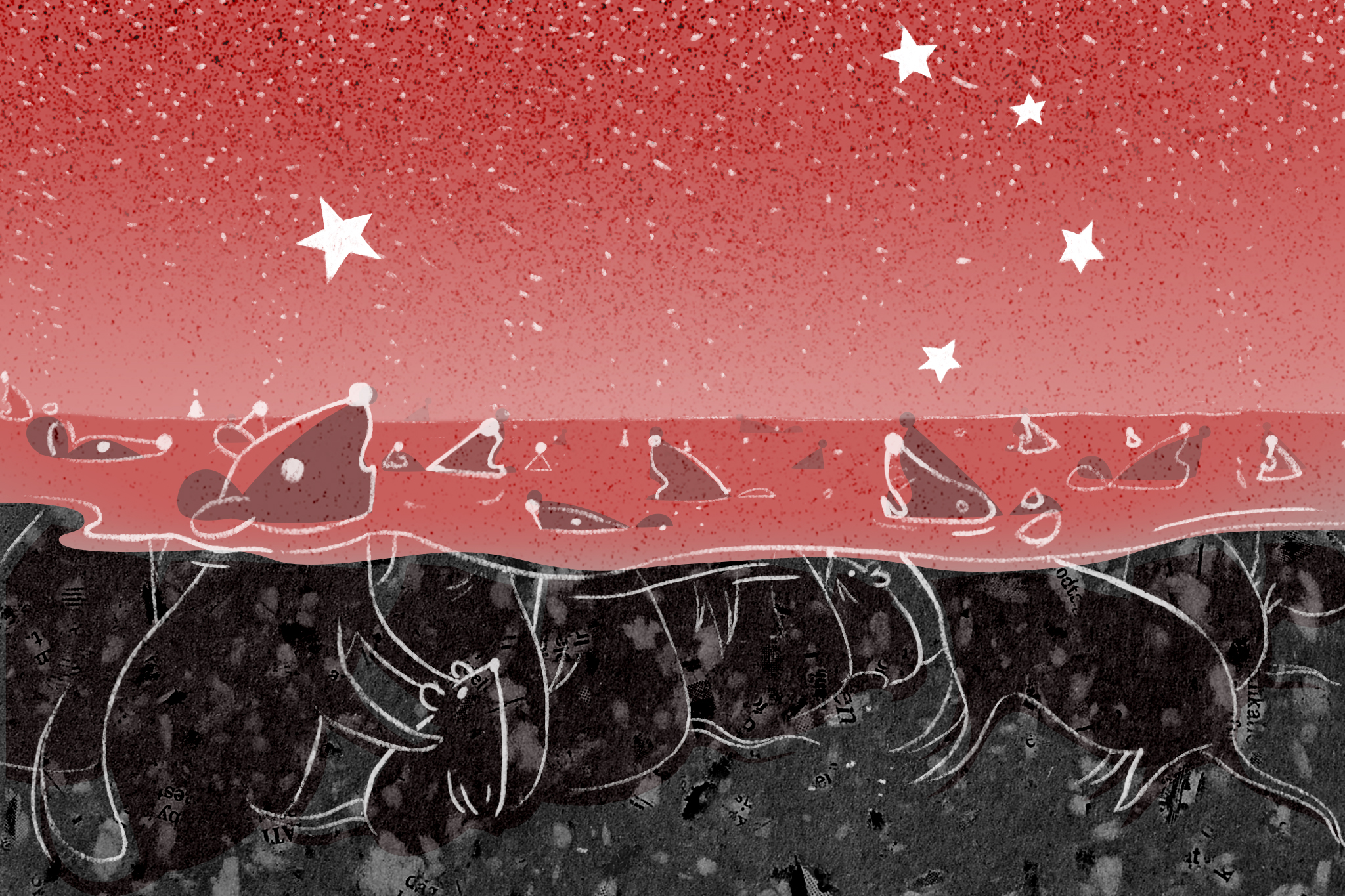黃宗潔書評〈掉進裂縫的人──《低端人口:中國,是地下這幫鼠族撐起來的》〉全文朗讀
「這裡是好地方,也是不錯的城市,但所有的好地方都需要付出代價,而且是所有好地方都必須付出的代價。」(尼爾.蓋曼《無有鄉》)
尼爾.蓋曼(Neil Gaiman)曾在奇幻小說《無有鄉》之中,以其精湛的說故事功力,帶領讀者進入一個不可思議的「下層倫敦」的世界。英國身為全世界最早邁向現代文明的國家,倫敦的上層與下層世界,當然不是以地表為界的城市建築與地鐵網絡之區別,而是一個在城市秩序與歷史暗影交錯之下,充滿種種矛盾的老靈魂。
諷刺的是,當主角理查回到地上世界,向朋友描述自己的經歷時,朋友說:「這個會有人從裂縫掉進去的下層倫敦,聽起來比較像是你虛構出來的。理查,我見過那些掉進裂縫裡的人,他們就睡在河濱路上的商店門口。那些人根本沒去一個什麼很特別的倫敦,他們都在冬天裡凍死了。」
掉進裂縫裡的人,並沒有那扇奇幻的門可以遁逃

「他們都在冬天裡凍死了。」直白地指出了真實人生的殘酷真相──掉進裂縫裡的人,並沒有那扇奇幻的門可以遁逃。但隨著此種「下層居民」人數的不斷增加,交錯繁複如地底迷宮的場景卻不再是奇幻的虛構小說,而是在某些城市中悄悄滋長的現實。因此,派屈克.聖保羅(Patrick Saint-Paul)的《低端人口:中國,是地下這幫鼠族撐起來的》,如同一部中國版的《無有鄉》,跟隨聖保羅的腳步穿梭在陰暗潮濕的「鼠穴」之中,我們看到的,是迥異於故宮、鳥巢、水立方等「地上北京」之外的另一個世界。
這個裂縫中的世界往往燈光慘淡、充滿霉味、潮濕惡臭、空氣稀薄,不免令人懷疑誰想長期棲身其中,這還是生理層面的部分;就心理學的眼光來看,地底洞穴也很難令人心曠神怡。巴舍拉在其知名的《空間詩學》一書,就曾對居住者如何透過想像「建構」與「重構」屋內空間進行析論,他主張,屋頂或鄰近屋頂的空間(如閣樓)因為具有遮風擋雨、免於受到自然侵襲的功能,較常被賦予「理性」(rationality)的意象;相對地,地窖因「帶有潛伏於地底的力量」的特質(partakes of subterranean forces),就成為更接近死亡的「非理性」象徵。因此,對於這兩個似乎都帶有神秘色彩的空間來說,地窖顯然比閣樓更容易帶來非理性的恐懼。這說明了何以恐怖小說和電影中,往往都有那麼一道通往地下室,會發出嘎滋嘎滋聲響的殘破樓梯,而且不信邪或好奇心過剩的主角,毅然前往地下室一探究竟的決定,通常都不會有什麼好事發生。
這群龐大的北京「鼠族」,為何又如何棲身於此
換言之,在有選擇的情況下,多數人通常不會想要選擇陰暗、潮濕的地底空間做為居所,這群龐大的北京「鼠族」,為何又如何棲身於此,他們的存在揭露出一個什麼樣的當代中國之圖像?就成為聖保羅《低端人口》一書所欲探究的核心命題。
然而,這些地底通道所交織出的,不僅是一個充滿各式潛規則的地下社會,更是環環相扣,混雜著政治、經濟、權力、階級等因素所構成的當代中國之異質空間。其複雜難解的程度,讓聖保羅在本書一開始,就直言「寫鼠族是個錯誤的決定」,因為「寫這主題面臨的障礙實在太多、太巨大了」:居民傾向隱忍以免失去僅有的棲身之處、地下世界的經營者在灰色地帶小心戒備、官方則嚴密慎防「敏感話題」的挖掘。更重要的是,相較於其他「臥底」之姿進行研究的社會學家或記者,他清楚意識到自己毫無任何可能偽裝成中國人。
但是,本書最特別之處,或許也正在於聖保羅對於自身書寫位置與限制的高度自覺。如同任何關於揭露底層生活之書寫,總難免要面對如下的質疑:寫作者的階級與知識背景,註定與他所欲召喚關懷的族群有著根本上的差異,那麼,透過有限的訪談或觀察,是否足以真正進入書寫對象的世界?就成為巨大的挑戰。一如班.朱達(Ben Judah)在《倫敦的生與死:一部關於移民者的大城悲歌》這部以當代倫敦移民者圖像為主題的作品中,開宗明義宣布的:「任何事情我都必須親眼見證。我不信統計數字,不信專欄作家,更不信那些自以為是的城市代言人。」但他透過穿起乞丐裝、到地下道睡覺,記錄人們對話的「親眼見證」和「親身體驗」,也仍然只會/只能是短暫的「扮裝」。
敘述和揭露,最後會否僅是將底層他者當成獵奇對象?
因此,聖保羅一方面努力想要被他所描述的底層之人接納,但另一方面又清楚意識到此種缺乏穩固基礎的「友誼」之脆弱,意識到自己無法適應或無法捨棄的生活樣貌。於是,當他探訪知名的鼠族人士王修清一家,看到黏膩的杯子、生鏽的水龍頭和亂七八糟的環境,他只剩下一個念頭:「要是這家人為我們準備了午餐,該如何拒絕?」當某位受訪者表示她不可能在自己工作地點的高級超市消費時,聖保羅則心虛地想著:
這間高級超市簡直是我們一家人剛到北京時的救命浮木。……每每結束了底層中國的深度踏查,從那些只能吃炒麵、水餃或喝碗湯的地方回到自己的世界時,我會帶著喜悅和些許罪惡感,品嚐一小塊洛克福藍黴乳酪。這款不協調的狀態引發一連串質疑:採訪這些住在地底的人、試圖想理解他們,卻連偶爾參與他們的世界、進入他們的日常都沒有,難道不會很失禮嗎?
事實上,他最後的確去「體驗」了一晚地洞生活,但地底宿舍大部分的人,因著這個生活空間及工作性質的高度流動性與不確定性,竟然都不在了。那個晚上,他想與鼠族居民「建立更深刻的關係、觀察他們的習慣,希望對他們的生活有更多的了解」的期待,全都失落在荒涼的地底迷宮之中。他只能屏住呼吸,「想像著在幾公尺高的地方等著我的浴室、床鋪和冰可樂」,熬過漫漫長夜。

這些誠實的自覺與自白,或許會令人疑慮,敘述和揭露,最後會否僅是將底層他者當成獵奇對象?只是為了讓讀者看到一個陌生化的地底異域?但我認為,正是因為聖保羅對自己在文化、語言、階級各方面,註定與他所報導的對象格格不入具有充分的自覺,對於自己「缺乏進行這項調查必備之自我犧牲的特質」有某種程度的自知,此種無法企近之艱難,反倒提供了一個「鼠族」議題之外的,有關非虛構報導寫作倫理的思考方向。那就是,我們並不需要「成為」他者,也有理解與同情的可能。社會報導並非舉辦體驗營,文化尊重更不是只建立在假裝愛上那些自己無法接受的食物,所謂接納,難道不是雙向的去接納彼此之間必然的差異,同時在差異中看見真正的多元性?
他們是沒有戶口的人,在自己的國家成為幽靈般的存在
因此,即使聖保羅自始至終都沒有「融入」鼠族的世界,但不代表他無能揭開「鼠族」的單一化標籤,展現地底迷宮如何可能成為進入當代中國此一複雜謎題的入口。這群棲身於不見天日的惡質地底環境之居民,來自四面八方,基於各種不同的理由匯聚於此,他們很多在家鄉有田有屋,也不見得完全是為了追求什麼縹緲的「北京夢」,但各種現實卻讓他們捲入這個巨大的勞動網絡之中:來自棗莊的蘇瑩,蓋房子的錢來自土地被沒收,但房子蓋完了,家鄉卻沒有能做的工作,只好和丈夫一起來此賺錢供女兒讀書;抱怨「我們村子的人還比較文明」的老鄭,在原本的村子也並非活不下去,但是為了兩個未婚的兒子,老夫妻仍然為了湊足兒子未來娶妻的資金(共四十萬人民幣)繼續工作……
這些辛勤勞動的身影背後,則是環環相扣的貧富不均問題、居安問題、留守兒童問題、隱藏在一胎化與人口高齡化背後的社會和經濟問題。他們是沒有戶口的人,在自己的國家成為幽靈般的存在,即使少數成功的案例證明裂縫中仍有往上的階梯,但特例畢竟是特例。一如書中所提到的建築師周子書,在花家地進行的地下室改造計畫,這項計畫曾經廣受報導,被視為活化地底空間的希望與出路,但是當聖保羅再度造訪時,卻只看到已被封閉的地下室,「房東」捲款跑了,充滿活力的地下社區終究像是被夢與想像虛構出來的無有之鄉。
本文作者─黃宗潔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系學士、國文學系碩、博士。長期關心動物議題,喜歡讀字甚過寫字的雜食性閱讀動物。著有《生命倫理的建構》《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