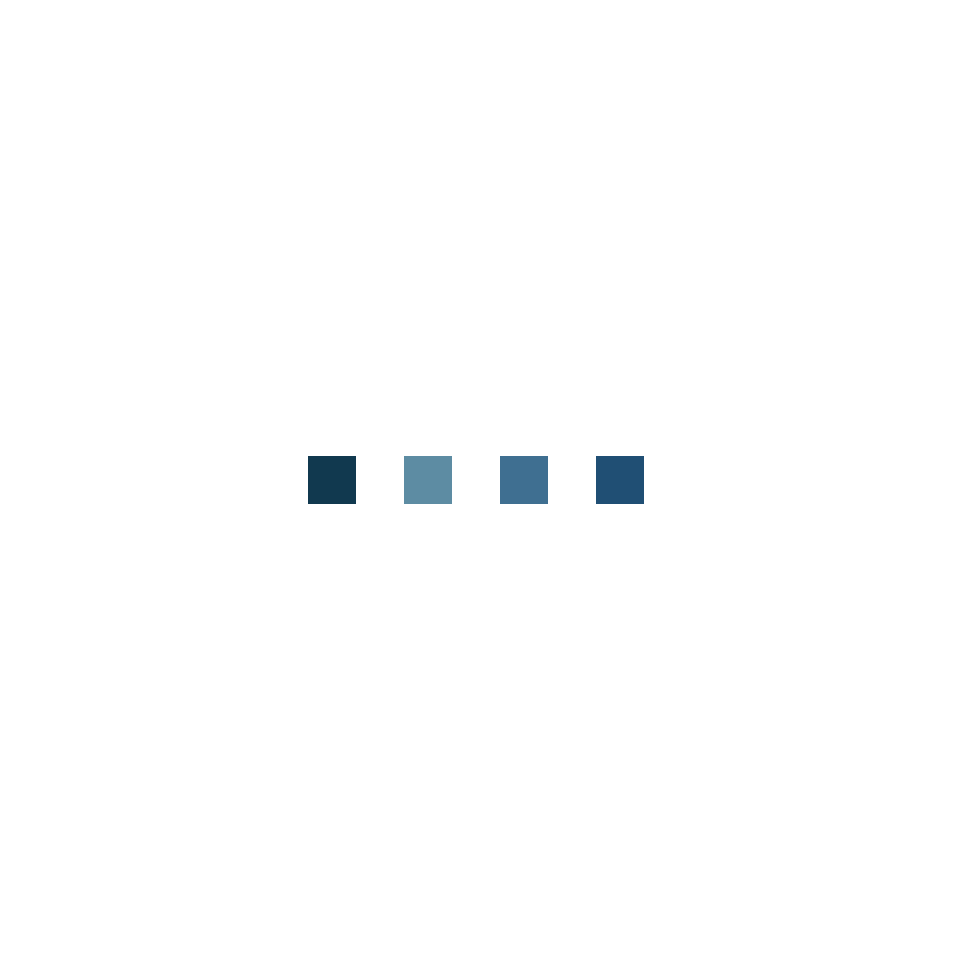阿比查邦2010年以《波米叔叔的前世今生》(Uncle Boonmee Who Can Recall His Past Lives,2010)拿下坎城金棕櫚大獎,這次他帶著自己的「狂中之靜」(The Serenity of Madness)展覽來台,他靦腆地說,自己還在芝加哥藝術學院念電影時,受到台灣新電影包括蔡明亮、侯孝賢、楊德昌等人的啟發,讓他重新看待自然、光影、樹木,能在台灣展覽也是對這些導演的致意。
阿比查邦的影像氣質神祕,遊走夢境與現實,敘事受佛教、印度教、及泰國東北的傳統影響,經常探討生死輪迴、神話,並隱隱加入對政治社會的批判。前作《華麗之墓》(Cemetery of Splendour,2015)讓一群士兵沈睡,唯有在睡夢中,意識的殘響可以不被政治掌控,既是逃避也是抵抗。
拍攝《華麗之墓》時,正好是2014年泰國軍政府再度發動政變,他不願意接受審查,臨時改變了拍攝地點,影片完成後也不想送審,因此無法在泰國上映。日積月累的挫折與沮喪讓他宣布:不會繼續在泰國拍攝劇情片。「2014年政變時,我覺得自己年紀已經大了,真的受夠民族主義,何時才會有真正的民主?如果泰王(拉瑪九世蒲美蓬)過世,全國人民必須守喪,無法拍電影,對投資人來說也是很大的風險。」
社會愈來愈不自由,人民上街示威被扣留,年輕學生聚集閱讀喬治歐威爾《1984》以創意反抗,後來軍政府禁止於公開場合閱讀《1984》。「真的很困難,我不是會上街示威的人,但我可以了解他們的想法和感受。」阿比查邦選擇離開,今年49歲,年近半百,他感覺自己沒有太多餘裕,必須去一個全新的地方刺激自己。
今年,與英國女演員蒂妲史雲頓(Tilda Swinton)合作的《記憶》(Memoria)在南美洲哥倫比亞開拍,主題牽涉當地毒梟暴力、地緣政治、記憶與夢境。「本來會有擔心,怕不能如期完成,又要與不同系統的劇組合作。但現在已經拍完,這次的經驗和感受很開心,就算觀眾討厭這部片我也無所謂。」儘管暫時不會在泰國拍劇情長片,但他仍關心國內的社會政治現實,會持續紀錄創作,美術館正好提供了另一個出口。

「狂中之靜」包含攝影、錄相裝置、影像日記,展覽主視覺意象是一個來自泰北的青少年,戴著鬼怪面具與太陽眼鏡,象徵鬼魅的拒斥。阿比查邦出生於泰國東北部的孔敬市,父母都是醫生,他排行老三,有一個哥哥、一個姊姊,孔敬大學建築系畢業後前往芝加哥藝術學院修讀電影。相較於南方曼谷都會與平原,東北是地處邊陲的高原,1940年代東北人湧入曼谷打工,1980年代開始又成為輸出海外的勞動力主要來源。阿比查邦說,東北的出身讓他來到曼谷大城後有自卑感,是開始拍電影,重新回到東北、泰寮邊界探索歷史後,才逐漸驅逐了自卑。
他的作品多帶有政治歷史探索。例如《煙火(檔案)》fireworks(archives)以薩拉鬼窟佛像公園為拍攝場景,影片開頭出現數位左翼民主運動者的人像,煙火的爆炸聲伴隨軍隊槍響、骷顱頭等死亡意象,正好反映了泰國社會以佛教立國、祥和寧靜的氛圍下暗湧的暴力殺戮。「當時的政治環境更嚴峻,他們用生命反抗政府,最後被當時的首相處決。我去過其中一個政治犯的家,他兒子已經七十歲了,父親坐牢、在獄中自學法律為自己辯護。」

創建這個薩拉鬼窟佛像公園的僧侶Luang Pu Bunleua Sulilat在1960年代被控為共產黨員,流亡寮國,而當時處決政治犯的首相至今在泰國各地公園中仍有紀念雕像,有民眾去獻花致意,「泰國政府一直沒有面對自己的歷史,我們一直沒有正義,也不能相信法庭判決,很多判決違反常識。現在甚至有不能批評政府系統的法律,非常可怕。」
藝術家在國家機器體系外開啟不同的記憶戰場。錄相《灰燼》(Ashes)以lomo相機紀錄泰國社會日常,隱隱用「112」這個數字暗指泰國刑法112條對皇室不敬的「冒犯君主法」;攝影《動力男孩(湄公河)》(Power Boy, Mekong)映照泰寮邊界、湄公河對岸的沙耶武里大壩發電廠,電廠為寮國提供電力,主要消費者卻是泰國人,泰國人一面反對興建,卻又離不開對其依賴。
2009年開始的「原始計畫」(Primitive Project)以納布亞村(Nabua)的青年為創作與田野調查對象,這裡曾是1960至1980年代泰國軍隊駐紮、清剿泰國共產黨的地方。女人被強暴、遭懷疑是共產黨的人們受到折磨,或逃入叢林中。冷戰結束後軍隊撤離,但轉型正義始終沒有發生,這段歷史也不曾出現在課本上。「我關注這些年輕人,因為我關心未來,他們的祖父、父親輩受到軍政權、警察暴力折磨,雖然有些年輕人現在只是關心自己能不能找到工作,有些人選擇去從軍。」

「原始計畫」延伸出的一件錄相作品《俳句》(Haiku)中,納布亞的青年們睡在與藝術家一起建造的時光機中,在睡夢中被催眠。面對現實困境,只有在睡眠裡才擁有全然的自由。
夢境是阿比查邦持續探索的主題。以前他花很多時間睡覺、做夢、紀錄夢境,「但近二年睡得比較少,一天只有四、五個小時,我比較淺眠,常醒來,所以睡前我會吃各種不同的東西,油、補品、西藥……。」訪問時,他打開一包中藥,聞起來有甘草味,以為他感冒了,他卻說:「這是為了睡眠品質。」原來他來到台灣也積極嘗試不同提升睡眠品質的方法。

在哥倫比亞拍片時,他也到秘魯嘗試古老的迷幻植物死藤水。「第一次很恐怖,吐得亂七八糟,感覺很糟,但隔天早上感到很清新,就像大病初癒。晚上我開始想起小時候被壓抑的創傷記憶,我重新面對、對話,明白這是死藤水的效果。後來又嘗試了第二次,有一段時間,我的意識進入到一個幾何空間,有很多房間開開關關,我在裡面進出,我也成為空間的一部分。我本來預期會看到比較有機、生物或植物的形象,但沒想到是這樣的,帶給我很大的平靜和自信。」
睡覺之外,阿比查邦的日常生活很簡單,不看電視也不聽音樂,反而對冷氣機運轉、風吹過樹枝的聲音更為敏感。起床後花很多時間做早餐,偶爾打坐冥想,然後工作。清邁的工作室養了三隻狗、一隻貓、十幾隻雞在周圍跑來跑去。

記憶是為了抵抗遺忘,問他:如果有一個絕對不想忘掉的記憶,會是什麼?他想了很久,說:「也許還是拍電影的記憶,我跟劇組共同度過開心、沮喪、壓力,但回頭看都很美麗。拍《熱帶幻夢》(Tropical Malady,2004)的時候,我們必須拍攝樹上的猴子說話,但拍攝時,猴子跑掉了,消失在森林中。訓練師很沮喪,第二助導很同情他,但我當時只在乎電影,我需要一隻新的猴子,所以我打給朋友:『你可以幫我找隻新猴子嗎?』這段記憶很模糊,我那時很焦慮,氣到開除這個訓練師。我需要記得這個,我當時脾氣很壞,拍片的時候簡直就像個獨裁者。」他說自己原本脾氣不好,是拍攝《戀愛症候群》(Syndromes and a Century,2006)前夕,父親過世,拍完電影後他開始修行,脾氣才漸漸改變。

一個藝術家與其作品,就像是從土地中有機生長出來的樹木,離開泰國後,他還能自在創作而不被改變嗎?「我很喜歡在哥倫比亞拍攝的經驗,我也在問自己創作能否更自由?例如運用二、三個人的小劇組,旅行各地,不一定是拍電影,而是沒有計畫的創作。」他是公開出櫃的同性戀,他自言母親一輩的思想已奴化,兄姊也較擁護君主政體因而有過爭執,他已放棄與家人談論政治。追尋自由,離鄉做夢的人,還是從不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