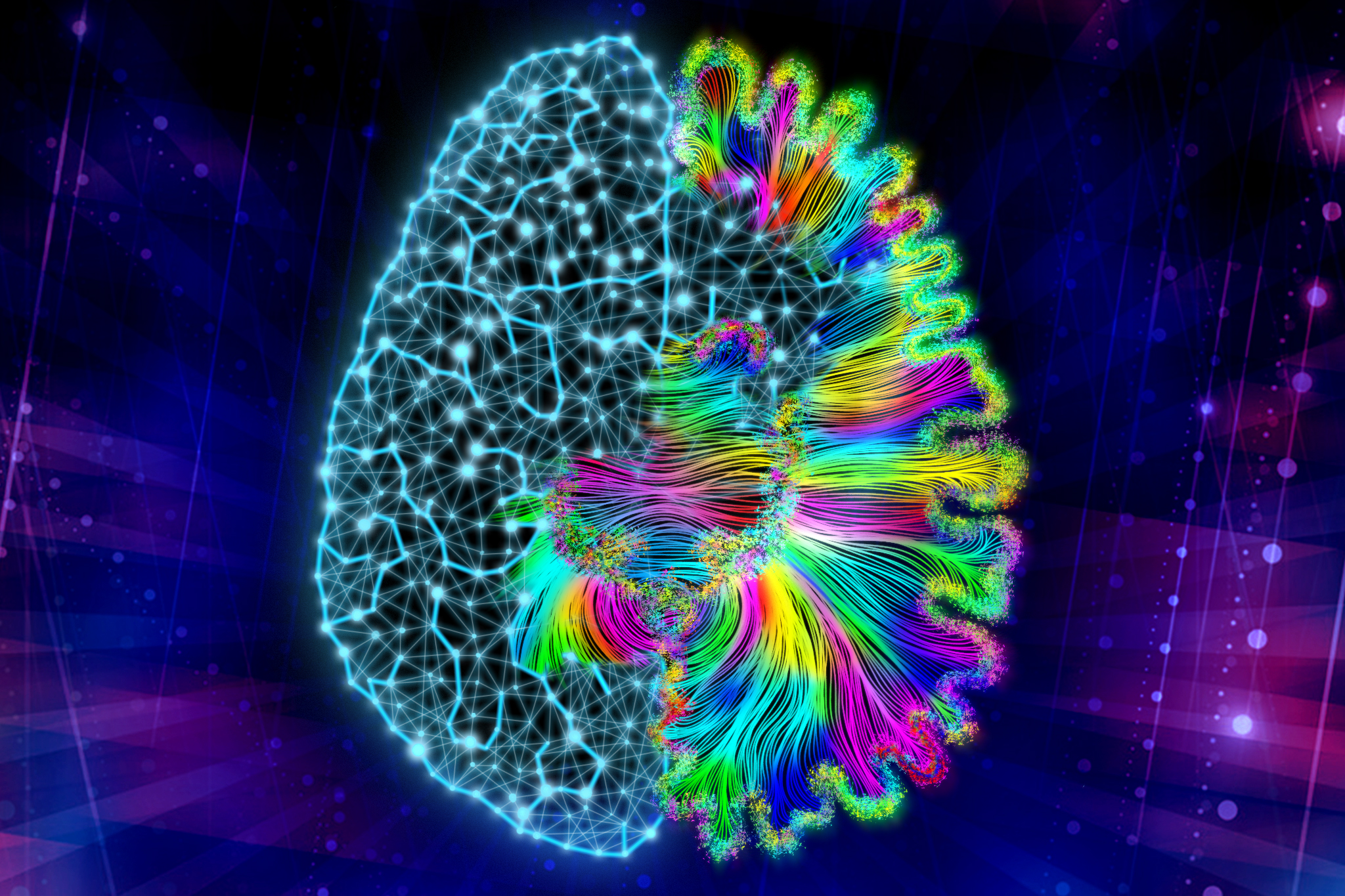王道還專欄〈為想像留餘地〉全文朗讀
蔡元培(1868-1940)是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部長,也是任期最短的教育部長。他只做了兩個月,可是他的教育理念卻影響深遠,「美育」便是他的遺澤。我國國民教育法明訂「國民教育以養成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其中德、智、體三目大概來自英國學者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甲午戰後嚴復讀了他在1861年結集出版的《論教育—智育、德育、體育》,深受感動,因而大力宣傳,呼籲以教育做為強國之本。後來梁啟超受到斯賓塞社會學──當時譯為「群學」──的啟發,認為中國人不懂得合群之道,才會受列強(甚至蕞爾小國日本)欺凌,於是在三育之外加上「群育」。到了民國元年,蔡元培以教育部長的身分再捻出「美育」,這個想法可以上溯至18世紀末日耳曼詩人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
所有其他的知覺形式都使人分裂,因為它們不是基於感官,就是基於知性;只有對於美的知覺才使人成為一體,因為他的兩種本性都必須與美協和一致。
這段話用柳宗元的文字翻譯,也許更容易明白:美感使人「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簡言之,美感使人超越塵世、現象界的羈絆。這也是蔡元培後來主張以美育代替宗教的理據。
然而在五育中,美育最難實施。別的不說,分辨美醜有時雖然不難,「什麼是美?」便是大哉問了;更不要說有時美醜言人人殊。而上美術館、聽音樂等美育實踐,往往揭露的是美感的個別差異。此外,每個人還必須以語文表達自己的經驗,師生才能相互印證──那可是必須鍛練的技能。至於美育的價值,根本難以考核,因為我們聽過的說教往往邏輯與結論全是想當然耳,例如前引席勒的話。
藝術創作力與藝術鑑賞力在人群中的分布有很大的起伏
因此有些科學家揭櫫神經美學(neuroaesthetics)的旗號,結合認知心理學與神經科學,尋繹美感經驗的神經網絡,以及藝術如何激發情感之類的大哉問,為美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思想、研究資源。一開始,學者利用大腦掃描儀器,的確發現了與審美經驗相關的大腦區域,例如音樂、繪畫引起的美感,似乎是前額葉特定皮質區域(OFC)的功能,已知它涉及與情感、報償有關的選擇。因此對於「美是什麼?」這個皮質區可算客觀的答案。
神經美學對於美感的個別差異也提供了睿見:因為人腦的個別差異非常大。過去兩百萬年,人腦的演化速率非常快,腦容量增加了三倍。演化速率快的結構,變異性最大。難怪藝術創作力與藝術鑑賞力在人群中的分布有很大的起伏。
可是最近發表的一個假說,與美育直接相關,特別值得關心教育的朋友注意。話說去年三月,英國皇家學會的生物學報刊出一篇論文,引起了學術辯論,勢頭方興未艾,甚至招徠大眾媒體的注意。論文作者是倫敦大學的博士後研究員朱莉亞(Julia F. Christensen),主旨是:藝術創造的愉悅可以培育健康的「選擇行為」(choice behaviour)。
追求愉悅與追求意義都能讓人覺得幸福
首先,朱莉亞指出現代生活的一個明顯特徵就是追求愉悅(pleasure)。表面看來,這個說法平淡無奇。但是她的意思是,由於價值觀的變化,以及工具的便利、價廉、又多樣,我們越來越容易獲得愉悅,無論食、色、藥物、電玩、手機等。後果是,我們也越來越容易沈迷於因而得到的愉悅。結果神經系統受到影響,使人在面臨選擇時傾向為愉悅而愉悅,無法對可能的選項做清明的思考,以朱莉亞的話來說,就是無法做出「健康的」選擇。
接著她指出,追根究柢愉悅感只是演化出來的學習訊號,目的在強化與生物需求有關的行為。換言之,愉悅只是行為的動機,而不是目的。為愉悅而愉悅,其實是「上癮」行為的特徵。另一方面,心理學的研究早就發現,雖然追求愉悅與追求意義都能讓人覺得幸福,融合愉悅與意義的努力才能帶給人圓滿的感受。
而大腦中與情感、報償有關的邊緣系統(limbic system)有兩個網絡與選擇行為特別相干,一個是A系統,追求立即的報償;另一個是I系統,處理與身體過程相關的內部資訊,著眼於未來的報償與福祉。耽溺於立即的感官愉悅的人,往往A系統越發敏感,I系統越發遲鈍,他們的選擇行為因而不健全、不得體。更麻煩的後果是,耽溺導致的癮頭根本剝奪了選擇的自由意志。
真的有「沒有意義的」愉悅嗎?
最後,朱莉亞提出「藝術假說」,指出以藝術加強A系統與I系統的聯繫是可能的——證據之一是音樂家、舞蹈演員對於自己的內在狀態有比較準確的判斷。朱莉亞過去學過舞蹈,這個結論無異夫子自道。
對於這個假說,今年3月下旬同一份學報刊出了一篇正式評論,兩位作者分別在西班牙、丹麥的大學任教,其中之一(Marcos Nadal)還是朱莉亞的舊識。評論主旨聚焦於朱莉亞的基本假定。朱莉亞主張藝術作品引起的愉悅,與食、色、藥物、電玩等引起的愉悅,有高下之別,兩者的差異在意義之有無。可是真的有「沒有意義的」愉悅嗎?講究口腹之慾、享受魚水之歡怎的就「沒有意義」呢?事實上,創造意義是人類認知能力的最大特徵,也是人文創制的驅力。藝術作品的意義是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內在於線條、形狀、色彩,或者旋律,或者身體的屈伸俯仰。欣賞藝術的能力是教養的產物。
根據評論者,「藝術假說」的致命傷在於:已知的大腦機制並不支持朱莉亞的兩種愉悅觀。所謂的基本愉悅(食、色)與高等愉悅(金錢、藝術、助人、宗教等)涉及的神經機制是重疊的;所有的愉悅似乎都來自腦子裡同一套快樂系統。評論者強調那是神經科學的事實,而不是個人意見。引起新聞記者注意的正是這一點:自1990年起,認知神經科學便是流行文化中的顯學,學者怎麼會連這麼基本的事實都沒有共識?
美育的理念仍有論證的空間
根據紐約時報記者的報導,面對這個問題,學界可分為三派,一派主張藝術引起的愉悅與其他種類的愉悅都來自同一神經機制。第二派支持朱莉亞。第三派則聳聳肩,說不知道,或者根本不在意。
不過,藝術的愉悅,或說美感,涉及的不只是神經科學的事實,而是我們對於自己的理解,以及了解人的理想方法,因此科學家(或科學界)無論如何都得有個說法,以嘲諷、虛無的態度面對並不恰當。畢竟研究的金主是納稅人——現在沒有人拿自己的錢做研究的。
這場交鋒至少提醒了我們,美育的理念似乎仍有論證的空間。
作者小傳─王道還

台北市出生,從小喜歡閱讀,但是從未想過寫作,因為小學五年級投稿國語日報兩次皆遭退稿。大學三年級起意外接到翻譯稿約,以後寫作亦以翻譯為起點(意思是抄襲)。
在思想上,對於「思考」產生全新的認識,是在高二暑假讀了《西洋哲學史話》(台北:協志工業出版)、《相對論入門》(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兩本書。從高一起就對演化生物學發生興趣,後來以生物人類學為專業可能並非偶然,可是對科學史、科學哲學的興趣從未間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