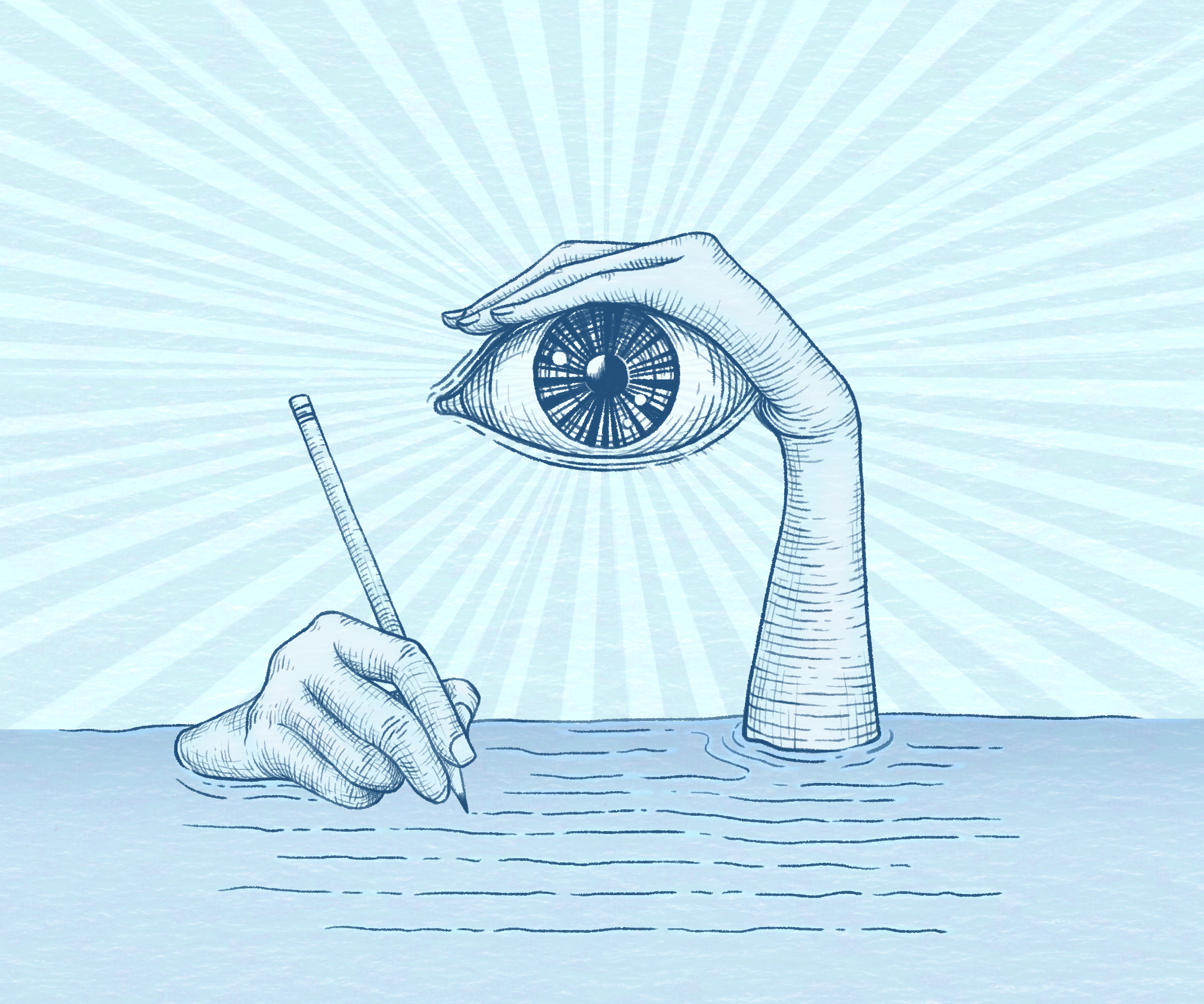房慧真談人物採訪與記者的角色
房慧真談文學創作與報導寫作
「想要擁有一顆真的心」,《綠野仙蹤》裡的錫人如果持續順著黃磚道往下走,前進2016年底,奧茲國會變作HBO影集《西方極樂園》,更多殺戮、更多血、更多裸露,人機對決不是決賽性能的優越,而在比憂鬱,怎麼生化人比人類更有感情,更多哀愁,更多愛……「你已經擁有心了」,錫人們不知道的是,那條迴路──黃磚道──才是真正的程式碼,被人類給覆寫了,改過了,看似迢迢大路的「由此去」其實是一種借徑--人類必須透過另一種物種趨近自己的過程去問「是什麼讓我們成為人」?所以故事裡生化人們的旅程,最後總是發現終點才是起點,而他們真正問的是:「什麼讓我們成為自己」?
「人物採訪」經常容易變得科幻,讀者希望這個分類是「複製人」、「生化人」──不能只是中醫診所廣告裡六尺四的銅人,徒有其型,貼幾個紅點經絡這裡按下去痛那裡按下會癢就以為到位了。讀者更要這類文章生白骨活血肉,他們要的人物專訪不只是素描,更要印象派(人物背後的影子代表什麼、一個手勢、一縷嘆息都饒有意境),同時要求作者呈現姿勢,更要內容有知識,想聽到豈止受訪者的現在,更要過去,最好暗示未來。他們要望見的不只是眼睛,是瞳孔後的靈魂。
複製人或者造物者:人物採訪的倫理

那種慾望是危險的。你看科幻小說裡所有機器人複製人生化人都在造反,稍涉人物採訪的記者都知道「複製」是種妄念,《時代週報》裡有一篇文章,是亞當‧索波欽斯基專訪《丈量世界》作者丹尼爾‧凱曼,他老兄就以調侃口吻點出這類文章的難處:「人物專訪,這到底是什麼?一堆不全是事實的內容,加上偶爾觀察到的現象,最後再來個妄加評論?」、「用這種方式寫出來的專訪當然有瑕疵,但這本來就只是一種偽造,一種相較於本人根本不可能十全十美的複製。採訪者站在相對立場上,更想挖掘的當然是受訪者的生命缺口或人生挫敗,這樣的主題才能成為重點嘛!」
但我想說的是,人物採訪是一門「技術」,其實也是「倫理」──像不像、有沒有勾勒出特徵,乃至於要不要寫,該不該寫──這是採訪者和受訪者之間的問題。說實話,誰又真的認識誰,我連睡在我床邊另一個人都不太熟,你壓根不知道所謂的「像」是指什麼?因為讀者不知道「真實」──記者所模版之物為何。
作為一介平凡讀者,你想讀的,首先是「人」(要先符合你想像,這個行業、這個情境,之於這個人的種種傳聞),然後才是「那個人」(超脫你的想像,有其特殊性)。而房慧真《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的厲害之處在於此。在於他本來可以完全不在乎此。他用技術證明了,他的人物訪問完全不需要「像」,而是直接讓你感到「他是」。那是召喚,而非臨摹。房慧真《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裡的本事是床上留下的凹陷,是被子推開後將散未散的暖意,也許是枕畔上的一兩根頭髮。是床空了,也許根本沒人呢,但你以為,他曾經依偎在你身邊。
房慧真是怎麼造人的?

前《壹週刊》時代曾有兩位記者是我心頭好。一位是李桐豪,一位是房慧真。李桐豪的文章好看,最好看在乍以為無愛之時,越有距離越好看,他要站在受訪者的對立面,去拆解去質疑,像在調戲他,一點點刺,一點點癢,越往對面站,奇怪越能寫進對方裡面。而房慧真則反過來,「愛著他」。書中一個愛的證據是,房慧真好不容易傻痴痴做完功課,卻因為受訪者陳為廷交代別寫而真的不寫,白白浪費了人氣話題(而同週刊另一名記者卻把他寫出來),「不要把受訪者當成一次性的商品。不要為求聳動,為了點閱率,而讓一次採訪毀了他一生。」。那比「像不像」更接近記者的倫理要求,可我覺得這也是房慧真的技術源。
她全心全意去「愛」,愛到想為受訪者留後路。但寫的時候,又要不留餘地,於是房慧真這個愛又有點扭曲,扭曲得像是偵探小說裡緝凶者和兇手的關係,以她的說法是「像花豹緊盯落單羚羊」,那是一種糾纏,你跑我就追,甚至,你去揣想他為什麼如此,「你要用兇手的思維去想」,用他的眼睛去看。這實是一種恐怖的心靈改造工程──在短時間內變成他。看受訪者一切所講所寫的,聽他所聽的,甚至,「我會為他選一首歌,寫稿時成天聽到爛」,那個愛,高強度,很殘忍,非把人逼到牆角不可,然後抓大放小,小的都不放過(「細節最重要」。他強調),可關鍵時刻又默默撇過頭,寧可全部失去。
恐怖喔恐怖,房慧真在逼近。但逼誰呢?《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書名出自西西《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書中多篇採訪同時附有「後記」,又有別冊,並且有超乎篇幅關於學運時的心情記錄和現場素描,那時你會發現這本書的野心遠出於「人物專訪之結集」上,這本書真的是複製人啊,是「打造」一個人的紀錄,卻是作家房慧真製作出一個「記者房慧真」的功略本。
她揭示的是,房慧真覺得「記者」是什麼?科幻小說「人是什麼怎樣的東西」在房慧真的書中變成「記者是怎樣的東西」?在這本書裡,「記者」不只是一份活兒,一個行當,它明顯有超出技術之外的要求,它更關於品格,還有它身為作家以及一個學院出身,一個社會運動者自己的堅持。亦即,一切又回到「倫理」──對於像房慧真這樣能動用大規模寫作技術彷彿好萊塢特效去憑空「打造一個人」的書寫者而言,她堅持的「倫理」反而成為不能繞過之路──不妨說,「記者」成了房慧真的途徑,她的路,她的技術之道(怎樣通往採訪之路),也就是她的信仰之「道」了。
大凡道之物,不能照做的,只能參考,求道者會往尖端走,那是孤獨的道路,若不是無限延展趨近「原來是這樣的風景」之「靜寂的峰頂」,不然就是中道崩阻半路摧折。而那追求的過程,就是藝術的誕生。《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的藝術性,我以為是在這裡,那是一個人類的孤獨之旅。她用盡一身技術通向他人的同時,其實是通往孤獨的自己。把自己逼往不可能之境。而報導可以學,只有藝術不能學。這本書則介乎可學和不可學之間。介於記者和作家之間。它好看,在於其中有人,不只一人,不只受訪者,還有記者本人。受訪者的故事是33個散篇,而訪問者的故事則是大長篇──暗記菜鳥記者如何從自稱「訪問白痴」變成痴狂,那是什麼,那也是故事。全書在訪問30人之外,又送你一人,訪問房慧真本人。
怎樣製作一具有血肉的身體;文體即身體
現在我們可以回頭看《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為什麼好看了。她動用哪些技術?我倒是發現,原來人物專訪需要「複製」的,不是受訪者的面貌,而其實更仰賴敘事的文體,亦即,這個文類,要寫得好,某個方面,搞不好更依賴文學的技術。不信的話,你看房慧真怎樣布局,她很慎選開端,那不是隨便安排的,專訪的開頭經常成為通篇文章的隱喻或象徵,打出一束光,讓你眩目,引起你注意,要你歸航,最後在文章收束時發現整篇文章是一個整體,是一座燈塔,途徑就是目的。目的構成途徑。

此外,房慧真擅長製造對比。她的訪問經常建立在人物自身的對立與矛盾之間,要說正,偏說反,想寫受訪者怎樣,偏要反著來,例如寫更生團契總幹事黃明鎮,偏從罪犯陳進興寫起。要寫黃明鎮之善,收尾卻收在這位牧者如何理解惡。又如她寫為曼德拉制定人權新憲法的奧比薩克斯,卻從奧比興味昂然逛起威權蔣老先生的中正紀念堂開始談起,並著墨於奧比薩克斯的生平介紹還偏偏在中正紀念堂裡展出。
以房慧真文章中的話來說,那就是「刺點」,或者是「白袖子上的汙點」,這其實是小說中人物建立的手法,很多小說中經典的人物其實是透過這樣寫法勾勒出來的。或者,我說顛倒了,小說的人物寫法,溯其源,可不正是小說家從對現實人生的理解中精鍊蒸餾出去的,人物專訪(非虛構文類)和虛構小說可能共享某個資源,可在書寫的操演裡,房慧真合一了,生化人會夢見羊嗎?作家和記者的視域結合在一起。而這類技術的好看往往在於,越有技術,越看不到。想要緊,偏是鬆,越有文體,越不見其身體。是美人了,還是穿起來的讓人遐想。這方面,房慧真是畫/話中人,也是擅畫/話者。
當然,本書還有一個閱讀的途徑是:「房慧真怎麼進化的」,如果重新將文章排序,按照成文的時間來排,讀者會發現,書中越早期的文章,隱然有一種制式:總是從受訪者初入眼那刻開始寫起,特寫、特徵的描述,一個吸睛的震撼,一個隱喻。但房慧真越到後頭,越自在了,她找到一種「借路」的方式──情境,文章裡不只是採訪者和觀察者,還有第三者,作家房慧真的身影也來入座。
她在說故事,怎樣去勾勒情境?閱讀書中房慧真兩度訪問達賴喇嘛和導演趙德胤就知道。有些記者寫一篇採訪就用盡全力,但房慧真偏偏要訪問同一個人兩次,而這第二次、第二篇,更精采了,她還有戲法變,還有事情可說,她甚至開始講故事了,達賴喇嘛的第二篇訪問從一個大逃亡開始,巧的是,趙德胤的第二篇採訪也是一個逃亡的故事,一個人,星夜下,馬鳴嘶,腳步聲,呼吸低喘,前頭無路,後頭是暗湧追兵,好看啊,你分不出來了,哪裡是現在,哪裡是過去,哪一段是受訪者嘴巴說出來的,哪一段是訪問者由受訪者過往作品或媒介中提煉的,那是一個整體,用情境吸引讀者進入,跟受訪者同感知,「複製是可能的嗎?」如果這時讀者如你我稍稍驚覺,可能會發現,「啊,原來,複製人其實是我啊!」否則,為何我們能感覺到受訪者的心?「想要擁有一顆真的心」原來是這樣來的。
房慧真抹消的,是讀者和觀察者的界線,受訪者更立體了,但文中不是有人,是無人,但你進入一個情境中。一個夢。卻比什麼都真。
問題:機器人想問「是什麼讓我們成為人?」不,機器人想問的是,「是什麼讓我們成為自己?」。問題是:「是什麼讓人物訪問逼近受訪者」?《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揭曉了答案。答案是,是放棄。你想變成他。你知道不是他。你吸收他的一切,你用他的眼睛看,你問蠢問題,你問聰明問題。但你永遠不知道,你才是對方最大的問題。而這一切,只是為了,到最後,一種放棄。
一種機運,因為採訪終究不是小說啊,不可測,你期待一個契機,就像寫作期待一次靈光,一道雷光打下來,你準備這麼多,只為了「他忽然打開了」,房慧真的諸篇採訪,透露出這種渴求,也津津樂道那個時刻來臨的時候。但你永遠不知道那什麼時候到來。所以你要準備好,甚至,抱著變成受訪者的痴想,或者,愛他。可這種不可測,才真正是靈光,那就是神之一筆。藝術等待這個靈光,採訪等待契機,它的箇中之味,《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抓到了。房慧真寫得讓你可以感覺那一刻到來的瞬間。我不知道有什麼比這還珍貴的,那是我覺得房氏人物專訪最好看的地方,她的房中術:「拍到雷電打下瞬間的模樣。」
而對房慧真自己而言,採訪是什麼?有趣的是,有一個詞彙在書中出現多次,那就是「抵達之謎」,他明寫暗寫,寫了又寫,用了多少次。我覺得這個詞彙彷彿才是這本書應該有的開頭──以房慧真的手法來說,一個暗喻。而這本書的結尾也藏在書中,是她自己寫到的:「等抵達本身終於成為謎」。人啊,本來就是個謎。無能抵達。但謝謝你帶我們經過。
本文作者-陳栢青
1983年台中生。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畢業。曾獲全球華人青年文學獎、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台灣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等。作品曾入選《青年散文作家作品集:中英對照台灣文學選集》、《兩岸新銳作家精品集》,並多次入選《九歌年度散文選》。獲《聯合文學》雜誌譽為「台灣四十歲以下最值得期待的小說家」。曾以筆名葉覆鹿出版小說《小城市》,以此獲九歌兩百萬文學獎榮譽獎、第三屆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銀獎。另著有散文集《Mr. Adult 大人先生》(寶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