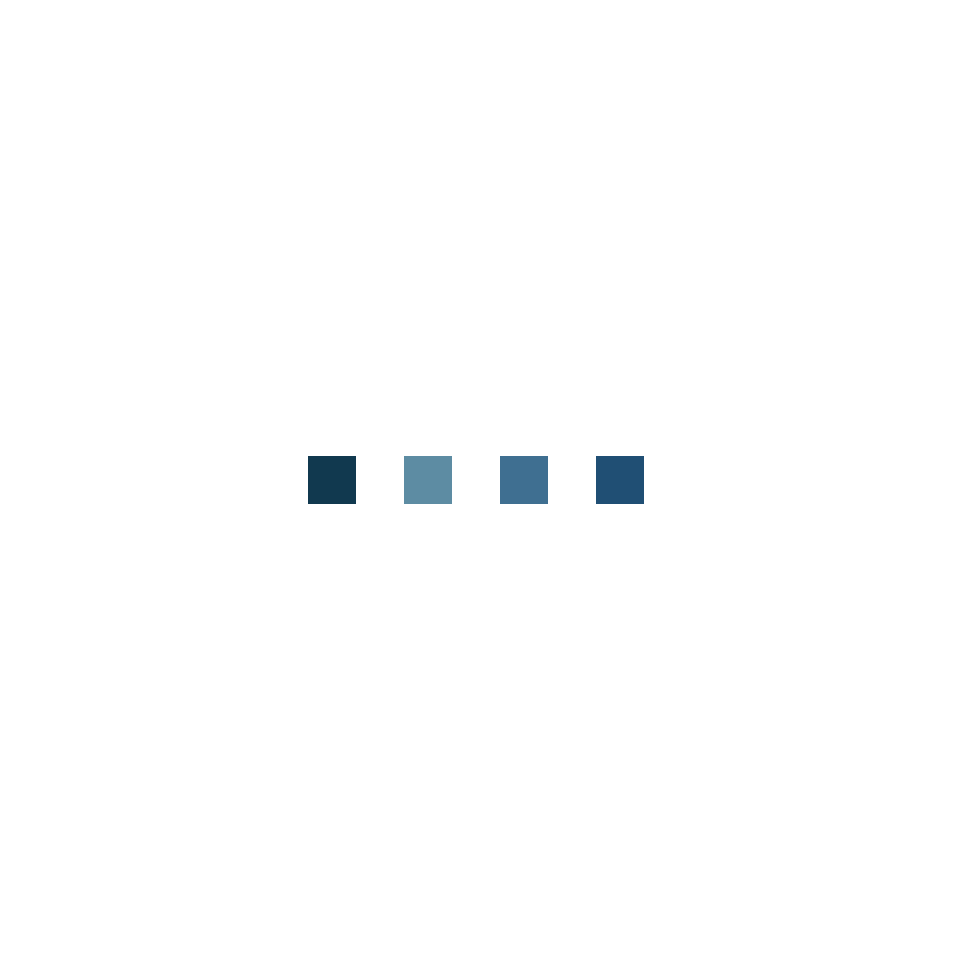西門之王 王明俊
「西門町是我第二個故鄉。」69歲的王明俊人稱阿俊,他從沒想過自己的命運和西門町的榮衰如此相似。上午9點半,我們和他約在西門町見面。他在西門町打滾57年,包括露宿街頭的十多年,3年前社會局資助他一天500元的「以工代賑」後,他開始能負擔便宜的租屋,但這裡才是他的「家」。
創業進斗金 瘋股賠千萬
他頭戴網帽加斗笠,T恤加休閒褲。出生於嘉義新港鄉,他說自己國小全校第一名,畢業上台北考初中,「沒考上不敢回家,後來就在西門町的西服店學裁縫。」台灣國語加上缺牙漏風,並不影響他滔滔不絕地說起往事。因為愛說話又不怯場,專門服務街友的慈善機構「芒草心」,有時請他擔任街頭導覽員賺外快。每次導覽行經萬國百貨前的廣場,他便指著對面的褲襪店說:「我在培爾蒙西服店學3年6個月,後來變師傅。」當年老闆培養他接班,他卻和人打架,為躲牢獄提前入伍,當一年海軍又逃兵,入獄一年後,再當2年兵才退伍。

「武昌街是電影街,以前也叫西裝街,西裝店最多時有68家。」70年代這裡是台北的流行娛樂中心,退伍後他開2家西裝店,「余天、康弘都是我的客人。」又說:「我女西裝和牛仔裝第一名,賺很多錢。」錢好賺,他接著開咖啡廳、電動玩具店、卡拉OK。他愛漂亮,2週剪一次頭髮,2任太太都是理髮師,後來乾脆開起理髮廳。他現在仍堅持天天剃鬍,注重儀容。
70年代也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全民瘋股市,「1978我做1億元股票,新台幣喔,光手續費就90萬元。」他說得開心,彷彿鈔票就在眼前;盛極而衰,那年股市崩盤,他賠了不少。1988年又遇上有名的「郭婉容事件」,政府宣布開徵證券所得稅,引發台股無量崩盤,「股票垮掉,我賠好幾千萬元。股票賣不掉,10元一股變3毛,成了擦屁股的紙,現在都擦光了。」
後悔打老婆 熱心助鄰居
再來是賭博和跳舞,「因為心情不好,天天在舞廳,一個月就好幾十萬元。」他的店一間間收起來,30歲人生就走下坡。80年代中期,台北發展重心轉往東區,西門町逐漸式微,就像他大起大落的人生。他此生最後悔打老婆,因為女人愛碎念不給他面子,2任老婆都被他打跑,3名子女不是逃家學壞,就是被前妻帶走。

「55歲開始睡街頭,因為沒錢租房子。」其實,西門町就是他的家,他的生活和這裡的人際網絡緊緊相繫,沿街沒有他不認識的店家、居民,四處都能哈拉抬槓。「鄰居有困難,我做得到都會幫忙。」他到處幫忙倒垃圾、做回收,每月可多賺1、2萬元,但是「我以前一天就花好幾萬元,忽然只能花這麼一點,不夠用。」這天中午,我以為他會帶我們去吃免費發放給遊民的便當,但他領我們去吃了一碗35元的雞肉飯,合點一盤燙青菜,一人約花50元。日子曾好過,三餐不想虧待自己。
夜宿睡騎樓 紙箱當床墊
下午3點,我們隨他執行「以工代賑」的工作,到里長辦公室倒垃圾,工作很輕鬆,目的是幫街友改善現況。工作結束,我們去他租處參觀,租金4,500元的房間約2坪大,他展示著做導覽時的照片,也訴說做街友的辛苦:大小便、洗澡、刷牙洗臉不方便,冬天很冷夏天很熱,蚊蟲多,點蚊香也沒用…「有時早上我坐在這掉淚。看著外面想,我以前是大老闆,怎麼現在睡這裡?」他坐在床上望向窗外,瞬間含淚哽咽,只看到模糊的未來,「所以我不敢往後看,只能往前看。」

褪色的西門町到了夜晚,還是熱鬧滾滾。聽到滿街嘈雜的音樂聲,他就開始在大街上扭動身軀,「我聽到音樂就想跳舞!」整天捧飲保力達B的他已然微醺,說話越來越大聲。即便露宿街頭,他還是要天天去舞廳。門票120元可以從中午跳到6點,舞廳有近百位6、7旬老人,看對眼就會邀舞,同桌的歐巴桑說:「這裡很好打發時間。」霓虹閃爍的西門町也是犯罪天堂,他事業走下坡後,近40歲加入在地的萬國幫當兄弟,「我斷斷續續坐了十幾年的牢,只有強姦猥褻和放火燒房沒有,其他都有。」監牢,是他第三個故鄉。

晚上9點的峨眉街尾,這是他流浪時的據點。我們蹲坐騎樓,這樣的視角只能看見熙攘行人快步交錯的雙腿,忽然有人輾過阿俊的腳卻渾然不覺,「腳趾給我踩過,伊嘛嘸感覺,路那麼寬,你娘咧,踩尬腫歪歪,明天不能走路誰的錯?」他忍不住抱怨,但,也習慣了,「青菜啦,甭計較!」在街頭,人情冷暖都嘗過,曾睡路邊被人丟水罐,也曾有人放錢在他床下,最多曾有1,200元,他猜自己以前常砸錢在舞廳,「可能是舞廳經理。」
仍想當老闆 七十才開始
今晚,為了體驗他過去夜宿街頭的生活,我們在騎樓用紙板占地,「睡街頭會下雨颳風,一陣強風把東西全吹走。這裡不好睡,來往的人很多,大陸妹的腳步聲都很大。」他邊講邊拆紙箱當床墊,「店家會送我紙箱,睡醒就收掉再拿去賣,每天都有新紙箱。」

夜幕升起,極樂西門正清醒,路人喧嘩、酒客爭吵、店家忙進貨、引擎呼嘯聲…閉上眼,「叩叩叩」的腳步聲不時伴著地板起伏而響起,每聲都是生命的威脅,深怕腳步聲就停在身旁。蚊蟲跳蚤環伺,想像力隨不安滋生,蟑螂老鼠爬進嘴裡,想著便全身發癢。夜尿時,最近的公廁距離200公尺,正好是從酣睡到甦醒的距離,廁所濃厚刺鼻的屎尿菸酒味,讓我又更清醒了些。我整夜難眠地掙扎,直到凌晨4點多才出現片刻寧靜。

5點天微亮,他已起床洗臉刷牙洗頭。上午7點,我們準時向里辦公室報到,整理垃圾、掃街,重複每日的行程,「我習慣這樣的生活了。」發跡在西門町,落魄也在西門町,他說:「不要同情我,也不要可憐我。」因為他有過別人沒有的輝煌,人生沒有遺憾。人生還是有期待,「我要當老闆,更上一層。我覺得我有機會,人生70才開始。」他想開一間讓所有人都能分期付款的西裝店,是夢想,也是目標,他沒有片刻忘懷當初西門町的事業王國。
孤獨行者 謝仁星
「不要把我當流浪漢,我是因為環境才會墮落到這裡,把我當流浪漢對我不尊重,我在國外讀到碩士,怎麼可以這樣對我!」這是62歲謝仁星的開場白。他說自己10歲移民巴西,40歲回台灣,錯過學習母語的黃金期,「我國語有點走樣,有人以為我是香港人。」2年前滿60歲,他得到「以工代賑」每日500元的收入,讓他能負擔月租6000元的房間,脫離十年露宿街頭的生活。
幼年住巴西 苦撐念碩士
午後我們頂著太陽,從大稻埕一帶往台北車站,重走一段他往昔流浪的軌跡。他頭戴帽子,T恤外是polo衫,再套件防風背心,脖子掛滿大串證件套,二個褲袋塞滿衛生紙,手上一袋塑膠袋和一把傘,傘能遮雨也能擔物,很實用,身上背三個背包,「這二個包包我一定要帶,裡面有證件和重要東西,放家裡被偷怎麼辦?」儘管有歸宿,他還是要把一整個「家」扛在身上。

他出生在迪化街永樂市場附近,家裡開成衣廠,4個哥哥、2個姊姊,他最小。父親經營不善,在他8歲時跑到巴西找工作機會。後來需要幫手,才陸續把子女接去巴西。17歲時,家裡在聖保羅開餐廳,他邊讀書邊在餐廳幫忙,「我那30年很苦耶,在那邊都被歧視,不要以為國外很好!」
他愛讀書,但家裡沒錢,不支持。他想學電腦技術,家裡有不同意見,最後跌跌撞撞念完建築工程碩士,「他們什麼都不懂,還干涉一大堆,一直叫我念我不想讀的東西……」說起這段往事他還有氣。32歲他把餐廳關掉,終於獨立自主,因為對建築工程沒興趣,他先去郊區的電腦公司上班,3年存錢買房,再去國小當數學老師,「37歲媽媽過世,我開始過著孤獨的生活。」母親臨終前,要他3年後回台灣,原因不能說,因為跟宗教有關,「講了你也不相信,等我成功了,再告訴你。」
立志要出書 積極找工作
他的休閒娛樂就是走路,沿途細數台北街景的變化。他說,其他遊民愛喝酒,生活亂,「我不喝酒抽菸,不吃檳榔,不簽牌不亂搞,走的是正常的路。」他的苦臉露出得意神情,「我喜歡安靜,坐在那裡想我要做什麼工作。」

「很多遊民不肯接受採訪,怕曝光,但我不怕,我要離開這個環境了。」他聲音微弱,字句全含混一團,「我要寫一本書,講我從台灣到巴西、巴西回台灣的完整故事,如何跌到谷底又從谷底爬起來,給人一個警覺,世界上沒有永遠的失敗。」
回到台灣的故事大致是:在幾間餐廳當廚師,但被老闆剝削;做保全、粗工,什麼工作都肯做,但年紀大,很多工作漸漸做不來;投靠親友,但沒錢就翻臉不認人,後來沒錢吃飯租屋,50歲開始流浪街頭。「這是很現實的社會,你沒利用價值就在街頭。」最初睡板橋車站,那時沒捷運,還有地方睡,後來到大安森林公園,再流浪到台北車站地下停車場,睡了好幾年。
我們走到台北車站,遊民們沿著短短的屋簷坐落,他們擁有各自一方天地。「我說句真心話,以前沒流浪時,覺得流浪漢很可憐。自從我接觸他們後,覺得他們一點都不可憐,他們根本放棄自己人生目標,好吃懶做。報紙打開,好多職缺,他們為何不工作?」他天天買報紙,看分類廣告找工作,因此說到其他遊民,他滿腹牢騷,「人會餓死,但不會做工做死。」「你要改變自己才能適應社會,不可能改變社會來適應你。」TED演講式的成功金句,時常從他嘴裡溜出,但他年紀大,工作實在不好找。
不信任他人 沒有好朋友
他說以前住台北車站,那裡的遊民老是喝酒鬧事,渾身髒兮兮,所以「我盡量不跟他們接觸,他們會利用你得寸進尺,我在台灣沒有好朋友,因為我不信任他們。」他離群索居在遊民的人際網絡外,卻過著類似的生活。在街頭,「你的朋友就是你自己」。

垂直往下就是台北地下街,「那裡有冷氣。」即便在台北長大,千篇一律的商店街和複雜的道路指引,地下街於我仍像座迷宮;但對街友而言,那是座樂園。這裡可遮風避雨,夏有冷氣,冬避寒風,洗手間、美食街、座椅樣樣俱備,只差不能睡過夜而已。接近商店街打烊的時間,他沿路撿紙箱,俐落地劈開封膠,那是我們今晚的床墊。
盼存錢開店 願翻轉人生
晚間9點,他把我們領到忠孝西路另一端,雖遠離遊民雜居的台北車站,但依然人車喧囂。我們蹲坐在鬧區騎樓下,宛如年久失修的壁紙,沒入身後灰土色的牆,沒有行人多施捨一絲目光。旁邊多了一對併肩卻寡言的遊民,感覺熱鬧許多。或許是很久沒有走上整天的路,才鋪好紙箱他就倒頭大睡。睡在大馬路邊,比較安心;但今夜的大馬路在施工,我徹夜看著鑽地機、挖土機、堆高機、壓路機來來往往,聽著巨大的轟鳴,仍是徹夜難眠。

清晨的冷風將我吹醒,謝仁星已靜靜杵在一旁,我們無言地看著稀稀落落的行人走過,在街頭擁有最多的就是時間。熬過夜晚,黎明應當來臨,「我還在修行。」他語調平緩地說:「我想1、2年內看能不能存點錢,我要開發另一條路,因為我不能永遠等著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呵。我要存錢開間小吃店,改變我的人生。」
上午9點,我們搭公車到錦西街的救世軍教會,10點領餐券,中午就有免費便當,「我有段時間一餐在這吃,另一餐吃50、60元的麵食店,錢不好賺,要節省花。」台北有很多慈善組織提供免費餐食,但不見得乾淨衛生,更遑論好吃,這裡的便當獲得他的認證,「我對吃的比較講究,因為我家是開餐廳的。」

中午我們在附近公園吃便當,他很久沒吃免費便當,吃得連粒米都沒剩。公園地上有塊破布,散落塑膠袋、寶特瓶和拖鞋,那是另一位遊民的家。我們想去看謝仁星的租屋,但他拒絕,「因為真的太亂了,而且我有自己的隱私。」不想回巴西嗎?「我不成功就不回去,如果成功,再回去看一看。」他老是「呵」一聲,聽起來是笑,看起來卻像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