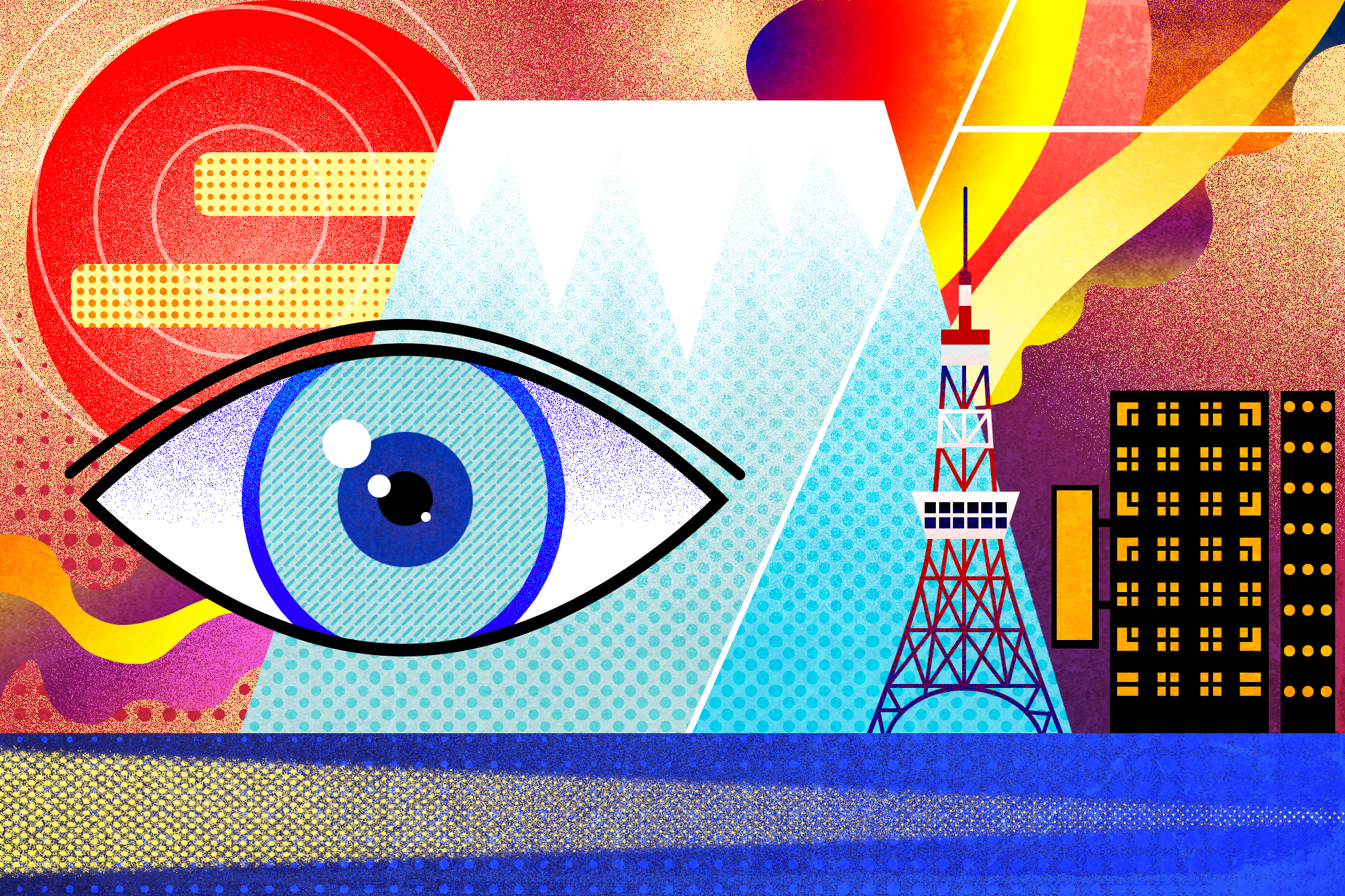廖偉棠書評〈錯誤窗戶看到的異樣風景──《情熱東京:1970年代回憶錄,日本最後的前衛十年》〉全文朗讀
70年代的日本前衛文化,好像驀地從一場大爆炸之後落入一個隱密的黑洞,驟眼虛無,驟眼又暗黑之花叢生,素來不分明。
它的前提是熾熱的60年代的落幕——60年代日本承載了鉅量的生與死之爆裂,從1960年10月12日極右翼少年山口二矢刺殺日本社會黨黨魁淺沼稻次郎事件始,左翼強烈反彈,正式開啓整個60年代日本抗爭政治序章;接下來的死傷者有1967年在第一次羽田機場事件被警察打死的大學生山崎博昭;1969年東大安田講堂守衛戰的學生傷者;乃至1972年淺間山莊事件那些自傷殘殺的聯合赤軍。
最後阿拉伯赤軍(國際赤軍,有別以殘酷整肅著稱的聯合赤軍),他們外逃轉而援助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策動著名的1972年特拉維夫機場自殺襲擊、震驚西方。但同時也徹底終結了「安保世代」的道德高地。
伊恩的「外人」身份決定了他的旁觀保有清醒

伊恩.布魯瑪1975年秋天才降落於成田國際機場,6年後他從這裡離開,在一片迷霧中看不見富士山,於是伊恩又發出了他6年都一直囁嚅的對日本隔閡的唉嘆——直到機師提醒他轉頭看另一邊的機窗——全書的最後一句說:「原來我一直搞錯了窗戶。」富士山在那邊呢。
不過,錯有錯著,也許正是搞錯了窗戶,伊恩.布魯瑪才能看到另一個東京,另一個70年代:不是左翼知識分子陷入虛無的70年代,而是邪魔藝術家踏刃而起尋找極端美學、迅速開到荼蘼的70年代。《情熱東京》以「新新聞主義」一般的非「非虛構」形式,書寫第一身的感官體驗以及傷害,同時兼顧宏觀俯瞰,填補了目前中文出版物對這個時期日本文化紀錄的空白。
這空白是雙重的,一方面是60年代記載如川本三郎的《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四方田犬彥《革命青春:高校1968》的戛然而止;一方面是當事人書寫的主觀私記,像寺山修司的《扔掉書本上街去》、橫尾忠則《海海人生》。伊恩的「外人」身份決定了他的旁觀保有清醒,而他對異色文化的狂熱又使他的體驗淋漓到危險邊緣,是這前衛的最後十年的有力速寫。
危險的魅力,就是這本書的魅力
危險的魅力,就是這本書的魅力。初到貴境的伊恩,僅僅懂得慨嘆「東京為什麼那麼像海市蜃樓!」這不但是東京本身的幻影感,這些戀慕東瀛色彩的好色外國人,自身就為海市蜃樓增貼一層層的濾鏡。在這個煉獄——不,海市蜃樓中穿行的混血但丁一樣需要維吉爾的引領,伊恩說那個引領者就是不懂日文的日本通唐納.李奇。
但和維吉爾不一樣,唐納.李奇是來增加危險而不是解除危險的,他曾經帶領伊恩深入日本真正黝暗陰褻的一面,我們都知道「陰翳禮讚」,谷崎潤一郎的美學發現在70年代有了新的演繹。
伊恩寫作本書的其中一個目的:尋找唐納.李奇的蹤影,其實是尋找自己青年時代的烙印,尋找西方在東方的投影。但就像他很快發現的一個事實:「在東京,現實與幻象的隔閡不是那麼清楚」——唐納.李奇表述得更精彩:「日本根本不需要迪士尼樂園,因為早就已經有一間名為東京的樂園。」伊恩補刀說:「這座城市的非住宅區的確有種主題樂園的蜉蝣時間感。」這蜉蝣在濁水中浮沈的意象,既是東京,更是癡迷於它的唐納與伊恩這樣的人的形象。
這種人有的是伊恩命名的「性難民」,唐納是代表之一,伊恩自身也曖昧地承認自己是雙性戀者。那些「性難民」同時也是自身祖國文化的流亡者:藝術難民。難民天然有尋找法外之地的本能,於是1970年代的東京就為他們而設。
三個不同的夜晚提醒了他洗之不去的「外人」身分
藝術家也有尋找「飛地」的慾望——一個藝術有「治外法權」的地方,如果說東京地下藝術圈是這塊飛地,劇場和闇黑舞踏則是飛地中的飛地。伊恩對自己在這兩者的體驗描寫得精彩絕倫,令人震撼,尤其是他隨傳奇戲劇大師唐十郎的劇團巡演的戲劇性經歷,遠遠蓋過他在電影圈沾染的點滴虛榮。
也可以從中看出一本1970年代的《菊花與刀》,從寺山修司、大野一雄、土方巽、立木義浩這些響噹噹的名字到刺青師二代目彫文、「人體泵浦」這些三教九流匠人,無一不在闡釋著菊與刀精神的延伸與蛻變。伊恩明顯從後者的「俗」中更如魚得水,挖掘一個有別於他之前的戀日洋人的異托邦,顛覆那已經在西方流行超過百年的浮世繪情調。
其實,這也是劇場、舞踏的日本與電影的日本不同,前者強烈的肉身存在感無時無刻不把美學意淫拉到具體的撞擊與傷害之中,而這是70年代殘酷人生的直接呈現。電影的日本秉承傳統的克制、形式主義和意在言外,即使寺山修司的電影都難以避免。伊恩自然被前者吸引,因為只有前者可以回報他意欲尋找另一個日本的激情。
不過,三個不同的夜晚提醒了伊恩他洗之不去的「外人」身分。一是京都大醉之夜,裝雅的洋人終於回歸本色;另兩個分別是和麿赤兒的大駱駝艦舞團、和唐十郎劇團的巡演,都以現實暴力告終。伊恩接受不了戲劇之中審美化的暴力蔓延到團體中人與人之間,更接受不了這種暴力最後終止於傳統的階級、抱團意識之中——唐十郎對他不從眾參與暴力的判決就是:你注定是個普通人。
這也是一篇《論外國人》,以戲劇的形式
藝術特權、師長特權、本土特權,說不清哪一個惹怒了伊恩,但肯定他對本土特權最敏感。「外人」始終需要神話加持去維持他對進入日本的幻象,但他無論多麼努力也只不過是一個被特權眷顧的「外人」。最終,「他在扮演日本人」才是伊恩的戲劇主題,「某些時刻,說外語的表演者覺得自己正背離了自我的某個部份……外語就像是一張面具,背後隱藏了更真實的東西」,伊恩說的是自己,但這點仍是唐十郎的《童女的面具》裡的腹語術者與他的傀儡提醒他的。

因此,這也是一篇《論外國人》,以戲劇的形式。伊恩的演藝生涯在他扮演一個「俄國人飾演的美國午夜牛郎」名叫「外人伊旺」到達巔峰,但也正在此,一個日本演員提醒他一條悖論:「如果你是外人,就不可能演外國人」,就像歌舞伎裡的女人只能由男人扮演一樣,「外國人」只能由自己人來演,當伊恩暴露出他不是「自己人」的時候(基於一些東西方的立場差異),他的演藝生涯當然也會到頭。
在伊恩黯然離開日本之前,最後二章調過來,寫自信的日本人來到紐約成為「外人」的情況,這個例子就是唐十郎。伊恩幾乎是帶著報復的快感去描寫自己的這位師傅在紐約格格不入,只能飾演自己:一個日本前衛藝術家的樣板。
這是復仇嗎?還是和解?伊恩最後感傷得無從判斷。「情熱東京」這個命名原來跟他的第一部電影《初戀》的命名一樣,是個反諷,內藏著的到底是伊恩迷戀的粉紅色情色電影裡必須的絕望。風景畢竟是風景,看風景的人也在橋上看你,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本文作者─廖偉棠
詩人、作家、攝影家。曾獲香港文學雙年獎,臺灣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春盞》《櫻桃與金剛》等十餘種,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散文集《衣錦夜行》和《有情枝》, 攝影集《孤獨的中國》《巴黎無題劇照》《尋找倉央嘉措》,評論集《異托邦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