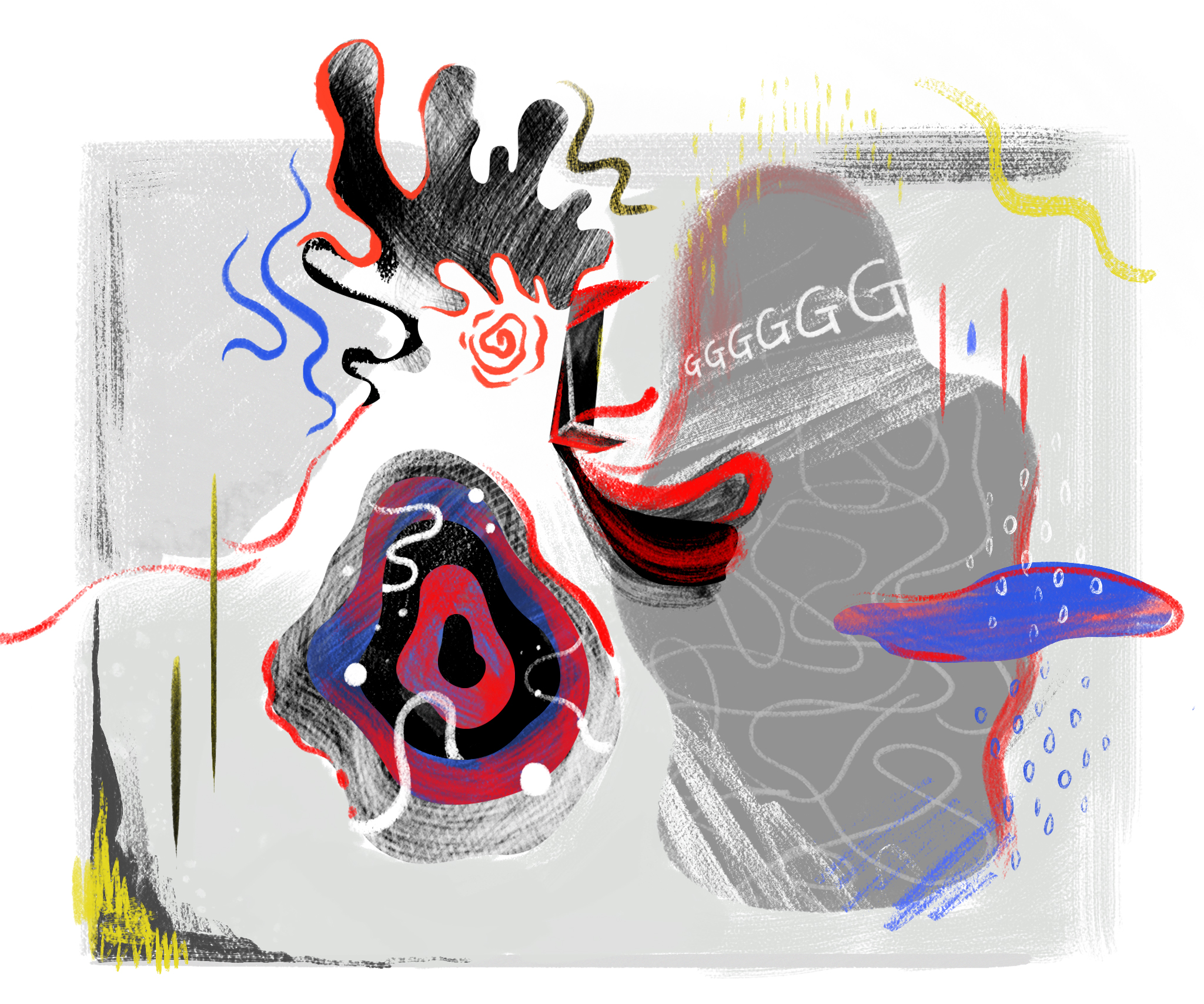陳栢青書評〈變成一個佬──《匡超人》〉全文朗讀
駱以軍談《匡超人》成書過程和創作理念
有一部我反覆重看的電影是《麥兜──菠蘿油王子》,動畫裡豬頭豬腦,媽媽是豬同學是貓是牛是烏龜,小麥兜每天去春天花花幼稚園上課,一整個動物柔軟毛髮的氣味其實就是童年以及其失去的故事,所以《麥兜──菠蘿油王子》講了什麼?麥兜的媽媽麥太太說這故事呢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小朋友」,然後呢,「有一天起床,他變成一個佬」。
那其實是所有故事的故事。所有的王子,所有的偶像,昨日少年、鮮衣怒冠,是故事書翻開第一頁,睡前一雙雙晶亮的眼神,乾淨的腳踝,誰知道有一天早上起床,泡眼惺忪,揉著一頭亂髮,看見鏡子的那一刻,電光石火,時移事往,「變成一個佬」。
不只是老去而已,有一些內在的什麼質變了,妥協了,逐漸歪斜了……
「本來可以成為更好的人。」
小說家也邁入五十大關了,體驗也有了,被辜負,被丟棄,暗裡被捅刀

駱以軍的小說《匡超人》註定是一個不能重述的故事。旋轉跳躍閉上眼,章節和人物都很任性,這裡出來那裡進去,起得即時,戛然即止,章節之間似有關,若無涉,它不能滿足,或不必滿足我們對於單線故事、乃至線性故事的需求,《匡超人》是濾過性病毒,自己會長,是昨晚沒有回家的男友開口對你說的第一句話,「一旦開始說謊就停不下來」,但主要是,就我自己看,那就是變成一個「佬」的故事。
要回到小說家自己的作品來看,更早是2004年的《我們》,他說自己大學時有段時間像廢了,收到教授來信:「我不知道你發生了什麼事?也許你會非常自信清明,覺得你只是暫時處在第二義的生活,不久以後,你也許就會回到第一義的世界,但是……如果時日漸去,你永遠永遠活在那第二義……」
接著,是2013年的《臉之書》:「我極年輕的時刻,某一次領會,我們可以只活在第二義的世界,如果可以愉悅過完一生,但那時我就選擇了,在某間密室裡,我只過第一義的時間,它不能模糊、混沌、起毛、交叉換手,用廣告邏輯造成偷天換日……」。
終於,2018年初始,他給了我們《匡超人》,各路超人齊聚(一個殘障版的復仇者聯盟),連大聖爺都給請來了,但小說裡是這樣的篇章:「有些時候,你感覺自己活在『不配那個年輕時的自己該延展』的人生,活在『第二義』,光度似乎不那麼亮的時光裡。」
第二義的人生,小說家也邁入五十大關了,體驗也有了,被辜負,被丟棄,暗裡被捅刀,必然也經歷人世的那些觥籌交錯,密室耳語,看遍那些隔著肚皮的買空賣空漫天要價聯合主要敵人打擊次要……也對抗過,也有敗陣,《匡超人》裡頭的敘述者總是傻愣八雞,卻在某一刻忽然醒悟,終於,「自己變成一個佬」,在第二義的世界裡多久了呢?
小說的底牌,其實也就是整個文明
當然《匡超人》的野心更大,不只是讓敘述者「我」徒呼負負,寫個體的經驗,「忽然變成一個佬」的,還包括這個時代,有什麼在其中被換掉了,圖畫走向畫筆歪斜的那方,駱以軍著重寫幾個點,其一,中國現當代一張大花臉。寫那個顏擇雅說「最低的果子還沒被摘完」、「趕上好時光」的新起之國,怎麼回事忽然踏進變了模樣的變形記裡:「當代所謂中國人,其實靈魂的內在……讓自己變成不是自己,或有一天發現想變回自己」,「富起來了」但這其中怎樣偷樑換柱、偷拐搶騙,他尤其愛寫那些古董鑑證,換假做真之術。
其二,寫我們這座城,這整個島,彷彿是被揉掉了、偏離最初規劃的小說,「我就想寫一本像保羅‧奧斯特《布魯克林的納善先生》的小說,寫這二十年,我在台北咖啡屋晃悠的『追憶逝水年華』……並沒有想到我們坐這咖啡屋裡,飆各自的疾病,身上的破洞、歪斜、壞毁啊。」、「我想寫一個台北版的《洪堡的禮物》,台北的偷、拐、搶、騙,我多著迷那些,當然我們這座城市現在不行了……」










其三,小說的底牌,其實也就是整個文明了。
「那個房間裡藏著遠古的魔獸『最後的恐懼』」,駱以軍九零年代小說〈消失在銀河的航道〉裡將軍大膽進入魔獸的房間,卻發現「『最後的恐懼』不是惡魔或怪獸的嘴臉,而是個如貼心的愛人一般的能量放大投影機,把你内在的一切恐怖、驚怵、幻影和噩夢,投影而出,歷歷在目,直到你的堅持被耗竭殆盡。」成書於「最後的恐懼」後一個全新的世紀,《匡超人》重新說起「恐怖」,「恐怖被藏身在光纖電纜的巨量訊息傳播裡」、「我們這時代,所有對恐怖的不祥預感;或逃離危險的歡快;或解構體會一個遠大於個人心智規模的戰役、政權的崩毀、錯誤戰略的大屠城;捲在其中的那些大名字、各自性格的缺陷,乃共同肉搏形成的殘酷、死滅、恐懼、哀愁。這一切都投遞在一個網路的Youtube上」,於是任何人都可以輕易的點開螢幕,「你好像看見自己的手,以一種視覺不可能的裡外錯置,伸進自己的頭顱,插進自己的大腦,像撥琴弦在上億條光纖中撥尋是的,那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恐怖箱』。」
「最後的恐怖」就是此刻,黑洞擴張到最大已然開始塌陷
九零年代還年輕的小說家那時必然不知道,這個時代,以及時代裡的我們正進入他「最後的房間」,這就是消失的銀河航道後的未來──我們的當代,一個《發條橘子》「強迫你張開眼睛看」,而更高妙的是,這個強迫在不自覺之間,還有人可以依靠點閱率賺錢呢,問《匡超人》寫什麼,不如問他怎麼寫?怎麼寫構成寫什麼。那是無數時間的碎片。一個章節是一條時間線,或者到此結束,或在幾章後重起,人物此消彼現,情節與象徵時有重複,你不妨把它視為一個youtube短片,一個視頻,《匡超人》本身就是個巨大的文字youtube合輯,三十餘萬字體現我們當代的光怪陸離,糾結震顫的心靈史,集體潛意識,一切顛倒妄想,無明恐怖,遠方國家烽火炮擊那夜視鏡裡綠光流火、斬頭畫面、導演或藝人強迫道歉……可以變成自動播放或二十四小時接力看《中華一番》、《琅琊榜》,遠古的魔獸在現代成形了,「真實的感性,想像,其實是已經變形了的這個現代的時間分格、商品環伺、移動的便利、所有媒體的訊息殘影閃爍在我們腦前額。」
於是我們縱是孫悟空,科技推動那遠程火箭天宮衛星帶我們到未知之境,觔斗雲翻個跟斗轉瞬三千里,文明的大宴,跨過了線其實是緊箍咒,那背後影幢幢是《儒林外史》,是歷史內線交割與密室暗盤,是用刀叉吃人肉,你看《匡超人》到了終章卻是開腦要吃那猴腦宴。「最後的恐怖」就是此刻,黑洞擴張到最大已然開始塌陷,當年的小說多像預言,而原來「最後的恐怖」,其重擊處不是當年「把你內在的一切恐怖、驚怵、幻影和噩夢,投影而出,」不是那個youtube,真正恐怖的是,「直到你的堅持被耗竭殆盡」,什麼時候,我們竟就「變成一個佬」,我們老早,已經在最後的房間裡了。不是我們怎麼變成這樣,而是我們何時變成這樣?
無論文明、城市、人類的信仰,乃至他自己,全部被壓得扁薄無比
《匡超人》裡有五分之一的篇幅專寫那些古董器物的鑑定與造假術。那可以和周芬伶2017年出版的長篇小說《花東婦好》合著看,同一世代書寫者,談那些出土器物歷代文物,怎麼盤怎麼賞怎麼驗怎麼審美,頭頭是道,錦繡滿眼。但駱以軍花費大量筆墨,更專注在那個神乎其能的贗造之術,瓷器如何造假仿古,縫進動物身體、埋入糞坑、移形幻影,張無忌使出乾坤大挪移,在專家法眼下一揪一逃……「這種造偽的耗竭心力,抽離出他們所依附的那個『真』,本身已可形成一個獨立的文明。」
於是《匡超人》中每一篇小說,你可以把它當成瓷片,或是「磁片」,他自己在小說中借劉慈欣科幻小說《三體》描述「降維攻擊」來形容生活。「降維攻擊」是外星人的毀滅性武器,把活在三維世界的壓縮到二維裡,「使三維空間的一個維度蜷縮到微觀,從而使三維空間及其中的所有物質跌落到二維。」駱以軍在《匡超人》正以此嘆曰,一切被「降維」了,無論文明、城市、人類的信仰,乃至他自己,全部被壓得扁薄無比,「我們以為是活生生的時間,其實是贗品的二維世界。」在那些古畫古董瓷瓶上,那個china上,上頭技術多好,完全是高端仿古,整個當代的光怪陸離,狼性、假凰虛鳳、偷來暗去倒打一扒,被壓縮在薄薄的瓷瓶上,很真,很美,但又如何,就是薄薄一片,就是假的。就是個痰盂。
小說家把華夏文明的精神史、心靈史,這個大家心領神會的大寫China,箝進瓷器china裡。兩個china在此合一。
而我們就活在其中。第二義的。活在精神史的China或是生活史的china裡。在西山夜宴或是小橋流水中打躬做揖,謹小慎微,盤進那個複雜的人物關係裡,工藝日深,一來一往感情都那麼真,其實活得那麼扁薄、不值得……
(我們被設定好了)
(是誰把我們丟進去)
(我們是贗品)
(這一切都發生過了。)
洞有多少意象和辯證,小說家之筆在這大作文章
直到小說家寫道,「我的雞雞下方破了個洞」。洞在這裡頭變成了多重的小說裝置,那自然是小說家的拿手好戲,洞有多少意象和辯證,小說家之筆在這大作文章,洞是缺,但那個空洞是另一種滿。是入口,但也是出口,洞是破損,但透過痛去醒覺、窺探。乃至洞之洞──破掉的洞破掉了,作為一種形而上的完整,洞作為一種區隔。
但主要是,多了個洞,那使得這些凝結的(小說裡不停使用「餵魚紅蟲結冰」的譬喻,乃至某一章真的將整個台北封凍起來),僵固的時間片段出現裂口,諸篇小說也如瓷瓶破了洞,那時瓶裡是瓶外,這裡才看出小說家的真功夫,一切變成他的時間幻術,一個瓷片是一段時間,瓶裡瓶外,看瓶面畫的人與畫中人彼此錯身、交換,視角奇異的變動,那便是克萊茵瓶,是墨比斯環……他在小說裡調度無數時間炫計與典故──這麼說來,我擔心的倒不是讀者怎麼看不懂,我擔心的是,學者怎麼看得懂,譬如這個老王還是老黃老陳,搜索枯腸從現當代文學無比燦爛的天空想找出幾顆星星連結比附駱以軍好組成星座,但駱以軍這樣一個帶著台灣文學往前衝的火車頭,其實是台拼裝車!

未來孩子更直感的便能看出,這龍頭這引擎這火星塞,全都是現當代那些次文化流行電影電視影集漫畫啊,當學者調度知識庫艱難點出這是芝諾「飛矢辯」、阿基里德追龜論、是尼采永劫回歸.……這些孩子會跟你說,《匡超人》這段引用的典故我知道啊,是美劇《十二猴子》還是《瑞克和莫蒂》每集穿梭時空改變這個想不到變動了那個,引發種種時間悖論,是《啟動原始碼》,電影裡傑克.葛倫霍透過程式進入八分鐘後要爆炸的火車,一次又一次的大火席捲而來,在車毀人亡的困難中認出恐怖份子的臉,是《JOJO冒險野郎》,漫畫中黑幫老大「老闆」的超能力替身就是「克里姆王」,當此替身發動之時,老闆能預先看到所有的未來並進行選擇,相對的,「所有人會到達他所選擇的未來卻省略掉過程」,而他的對手,少年漫畫主角喬魯諾則寄出「黃金體驗鎮魂曲」,「克里姆王」讓所有人直接抵達「老闆」希望的結局,但「黃金體驗鎮魂曲」的能力,卻是「把一切歸零」,「老闆」在可能的未來死去的一瞬間,連「死亡」這一事實都歸零,於是「老闆」將在「黃金體驗鎮魂曲」的能力中無數次抵達死之終局,卻又重新開始,反覆在那些死亡的敘事中被刀砍火燒、被汽車輾斃、遭解剖……一次等於無數次,沒有結束等於另一種結束……
《匡超人》小說裡那些忽然轉場的大冒險或超展開,其實是對時間的一種幻念或空間的換場,這台拼裝車飆出極限的火花,是寫給未來的。
「時間在延長著,這不是最後一關了嗎?」巨大的春麗在台北城上空與越南軍官對打, 這是1993年10月駱以軍短篇小說〈降生十二星座〉,二十五年後,當春麗抬頭,看見的,卻是克里姆王。最後一關被先決定好了、一切都在反覆,甚至,一個新問題是,有最後一關,那「最初」是什麼?
「世界末日已經發生」之中,怎麼辦呢?有沒有可以修補故事的人?
就我來看,小說家擅玩時間幻術,他也許也發現,那關於初始與終末也是另一種時間幻念。在那樣追趕跑跳,在那樣整個文明的反覆重來,學不乖,趨向崩盤,身體敗壞,心智崩毀,「世界末日已經發生」之中,怎麼辦呢?有沒有可以修補故事的人?用小說裡的問法是,「但是詩歌呢?藝術呢?小說呢?人心裡那些美麗純淨的東西呢?」
這樣說來,《匡超人》標記駱以軍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袁哲生進入小說中,在小說之外,他明確感受到同代人,或一個書寫圈的存在,袁哲生之死讓這批小說家開始有意識的聚會。那個在小說裡總是懵懵懂懂,一副受氣包模樣的「我」,現實世界成為一個「義人」,繩結扭纏的捆頭,把大家結在一起,招呼聚會,連結同輩,照顧後輩。
而在《匡超人》裡呢,「譬如說湯顯祖,或張岱這樣的人,你以為他們的心靈沒有那種漫天星空全焚燒的景觀?他們本來就是在一個老謀深算耗盡你全部精力的文明裡,曲徑通幽找出放置那一小盞燈燭不熄滅全黑的方式。」超人們集體要去保護那個「所有人已經死掉了」的火車上的傻根(這次是兩部電影的梗),「如那個劉若英在搖晃的光霧中說:『別怕,姊會保護你。』那不正是你,傻根,唯一只有你,能夠贈與這列爆炸火車的集體八分鐘,一個讓人想流淚的,珍貴的什麼? 」一顆腎超人、肝指數無限高超人、重症肌無力超人、僵直性脊椎炎超人,以及破雞雞超人用他們疲倦的身體護著那道火苗,「這不是最後一關嗎?」春麗在台北城上空問著這個問題,還是二十五年前那張青春而童稚的臉,而「有一天起床,變成一個佬」的駱以軍此刻也許根本不會回答,他會拍拍春麗的肩,跳進那場難玩的遊戲裡,縱然肝指數過高、重肌症、僵直性脊椎炎,還是雞雞破一個洞,他會護在春麗的前面,用他自己的散文標題來說:
「化做春泥更護花」。
本文作者─陳栢青
1983年台中生。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畢業。曾獲全球華人青年文學獎、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台灣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等。作品曾入選《青年散文作家作品集:中英對照台灣文學選集》、《兩岸新銳作家精品集》,並多次入選《九歌年度散文選》。獲《聯合文學》雜誌譽為「台灣四十歲以下最值得期待的小說家」。曾以筆名葉覆鹿出版小說《小城市》,以此獲九歌兩百萬文學獎榮譽獎、第三屆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銀獎。另著有散文集《Mr. Adult 大人先生》(寶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