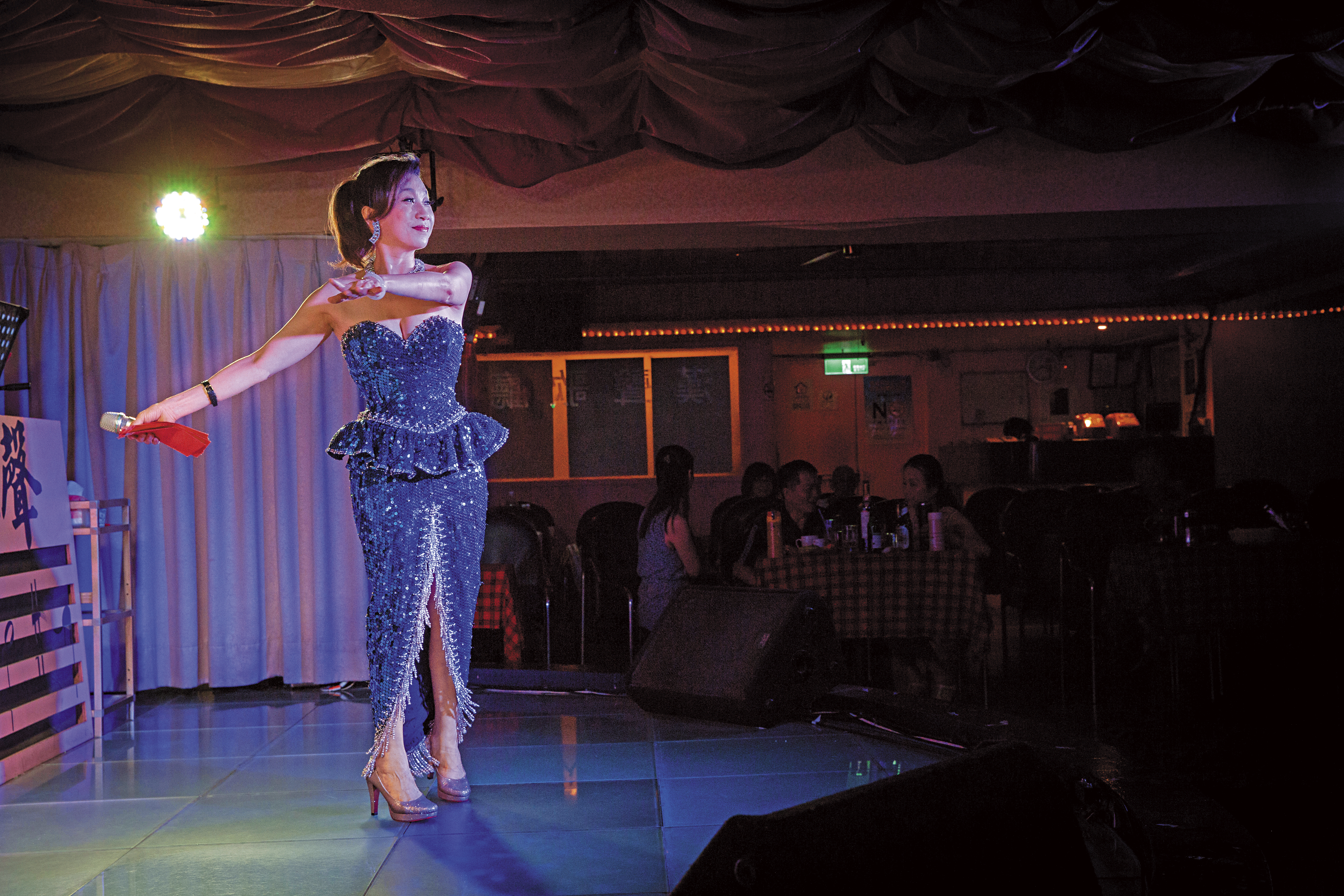車子駛在崎嶇山路,坐在後座的紅包場歌手今子嫣仰頭張嘴,表演一口氣灌完一整壺水。機不可失,同事啟動錄影機,我也加入計時。
我不碰酒又不想得罪客人,若遇灌酒,就拿出800c.c.的水壺和對方乾杯。
20秒,30秒,1分鐘,2分鐘…今子嫣竟連口水都不嚥。車子轉來轉去,水持續直灌她的喉嚨,我們擔心起來,要她停手別嗆著,她不為所動,最後只能關掉錄影機央求她:「姐,別灌了,我們不拍了。」
她抹抹嘴角的水滴,看看水壺,嘟起桃紅嘴唇嬌喊:「哎呀,還沒喝完吶,怎麼你們也和客人一樣?愛看我喝,又比我還緊張。」她說得柔柔軟軟,我們卻全無招架之力。
表演灌水前,今子嫣才領我們到三峽白雞山區的榮民之家,去探視她行3跪大禮認的義父葛爸。
她穿著迷你短裙,老榮民間的靜默被她10幾公分的高跟鞋踩破;她走到80多歲的葛爸身後將之摟住,又將臉頰貼上葛爸的。葛爸一愣,聽她拉長音撒嬌「老爹ㄟ」,猛地從渙散中回神,沉寂面容有了驚喜。

葛爸是大陸四川來的老兵,在台沒親人,因聽歌認識今子嫣,認定她是女兒後,長期到西門町歌廳附近大樓當夜間保全,好就近天天捧場。今子嫣說:「乾爹捧我的場30多年,每天午場、晚場都來,一場至少包3、5百元,一天2場要1000元,一個月給我的紅包至少就2、3萬元,就連生病住院也託人包紅包,就怕我遇到冷場。」過去老爹用紅包照顧她,現在換她把葛爸當親爹一樣照料,每月固定探視。
但紅包場龍蛇雜處,並非客人都單純把她當女兒或歌手。給紅包想要「回饋」的,不少;有機會就灌酒吃豆腐的,更多。「我不想碰酒又不想得罪客人,若遇灌酒,就拿出這瓶800西西的水壺和對方乾杯,剛開始客人都嗆:『妳做不到還是要喝酒。』後來都嚇到,反而勸我別灌了。」
「灌水躲酒」,是被現實和歲月練出來的。本名陳俐羽的今子嫣,父親也是榮民,母親則是養女,靠著打零工拉拔她與4姊妹,不時為三餐著落而苦惱。直到她16歲那年,踏進紅包場,家計慢慢有了曙光。
我回家跟媽媽說,客人包給我200元紅包,我們不用擔心明天的菜錢了。
「那時我被鄰居媽媽介紹去演電視劇,導演發現我不會唱歌,介紹我到西門町的紅包場練歌。」拿到第一個紅包,今子嫣樂壞了,「我回家跟媽媽說,客人包給我200元紅包,我們不用擔心明天的菜錢了。」
不太識字的媽媽對紅包場毫無所悉,只覺得接受別人紅包,好嗎?會不會被欺負?今子嫣一向以姊妹中的男孩自居,「沒事,沒事」,她答應媽媽會保護自己,也自此從演藝圈轉到紅包場。

其實,紅包場消費文化特殊,客人進場後點用水酒、水果、點心,不直接付錢給歌廳,而是包紅包給歌手,再由歌手買單。「通常每人基本消費是300元,客人少則包4、5百元,多則數千甚至上萬元,扣除桌面消費就是歌手淨利。另外,每月結算掛在歌手名下的消費業績,歌廳老闆會再分紅給歌手。」
樂隊老師問我要唱什麼key,我心想,唱歌就唱歌,哪有什麼key。

想賺更多紅包養家,自然要吸引更多客人捧自己的場。但今子嫣天生五音不全,「初期樂隊老師問我要唱什麼key,我心想,唱歌就唱歌,哪有什麼key,後來發現自己唱歌不行,就絞盡腦汁用動作和舞蹈讓表演有亮點。」
靠表演吃飯,服裝儀容不能馬虎。今子嫣家裡不只衣櫥,就連書櫃、廚房餐櫃也全擺滿秀服頭飾和首飾,「歌手登台比妝髮也比服裝,我會自己挑布、裁布去和裁縫師討論,有時為了增加舞台效果,還自己縫亮片、珠珠。」

細心經營加上嘴巴甜,20出頭歲的今子嫣已成西門町紅包場的紅牌歌星,曾在白金、山海關、安迪等各大歌廳駐唱熱門時段,擁有一批老兵歌迷和死忠粉絲,「巔峰時收入多少?這…方便說嗎?」她猶豫幾秒,才比了2根手指頭。一個月收入20萬元?她點點頭,「但那只是短暫的過去式。」
月入20萬元吶,就算今日也屬高薪,更何況是2、30年前。她卻沉默了,只用眼神回應,是嗎?
她從皮夾拿出一個藏了20多年的透明塑膠袋,「曾有其他歌手在我頭髮電夾棒黏上口香糖,我一夾,頭髮、電棒都黏住,眼看就要登台,只好整撮剪下來。」留著頭髮是想自我警惕,「這行飯,客人捧不捧場收入差很多,競爭、忌妒難免,我也曾有旗袍被剪破、禮服胸墊被拔走。」
今子嫣又陷入沉默,因為她心裡藏著更深的傷疤。「那年我才20歲左右,一個新加坡客人邀我去吃飯,我傻傻跟去,誰知喝一杯飲料就失去意識。」等她醒來,已衣衫不整,躺在旅館床上。
去看婦產科知道懷孕了,我還裝作鎮定,生怕醫生知道我被人下藥,覺得好羞恥。

「之後,我正常登台,當作什麼都沒發生過,月事卻遲遲不來,去看婦產科發現懷孕,我還裝作鎮定,生怕醫生知道我被人下藥,明明錯的不是我,卻覺得好羞恥…」她忍不住痛哭,「我甚至不記得那個人的臉,只能拚命在舞台上跳,看能不能把孩子跳掉。」後來在朋友陪同下,她選擇動手術讓孩子回到天上,「孩子無辜,但我實在不知道怎麼辦…」
紅包場的凶險面,讓今子嫣怕了也累了,遇到前夫追求,便動了結婚隱退的念頭。「結果,結婚一年生下兒子,我就發現前夫不只欠一堆賭債,喝酒就會發酒瘋,罵我『討客兄』,常常還有債主上門討賭債,我嚇都嚇死。」

婚姻告吹,又有父母孩子要養,加上姊妹需資助,她不得不回到紅包場討生活。但當歌手必須要有星味,還得留些遐想給客人,她絕口不提有過婚姻,更不准兒子喊她媽媽,「兒子一直叫我Aunty,喊我大姊媽媽。」她很是愧疚,「從前兒子想拉我的手,我都把他甩開,要他去找阿公、阿嬤。」
現在的收入和上班族差不多,但就算只有一個觀眾,我還是全力以赴。
說起現在和兒子的關係,她總算滿臉笑,「現在兒子大了,我也不想遮遮掩掩,逢人就介紹兒子,搞得他老抱怨:『幹嘛總提我。』」

接近下午3點,我們回到她現在駐唱的西門町漢聲歌廳。她身上像裝有開關,才到歌廳樓下,立刻切換回工作模式,逢人就嬌滴滴招呼,「大仔,好久沒來囉!」「董仔,今天想聽什麼歌?」
把客人送上樓,她若有所思,「紅包場就像個小型社會,有善有惡,重點在如何自處。」她似笑非笑,「過去我不跟人說自己的工作,現在我都很驕傲地表明在紅包場唱歌,靠唱歌養家有何見不得人?」
儘管這幾年老兵凋零,能拿到的紅包已大幅減少,她還是不忘精心打扮。「現在的收入和上班族差不多,但就算只有一個觀眾,我還是全力以赴。」
因此,她仍擁有不少歌迷,也被影劇圈看中,曾在張作驥導演的電影《醉.生夢死》中演出,近期又被網羅在電影《台北愛情捷運—西城童話》和迷你電視劇《花甲轉大人》當中演出。

我瞄了瞄時間,離她登台僅剩10多分鐘,不用先換裝嗎?她答還好還好,一溜煙又擠進人群,以水代酒跟客人乾杯。剩最後5分鐘了,她才終於進更衣室;再次出現,已換成22腰的露背低胸禮服。
登台前,她把水壺託付給我,「幫我顧好水,30年來,我只喝自己準備的水,別人給的飲料我是不碰的。」音樂一下,她唱著:「孤獨站在這舞台,聽到掌聲響起來,我的心中有無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懷已更改,我還擁有你的愛…」她眼神迷濛表情投入,唱的是鳳飛飛的〈掌聲響起〉,也是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