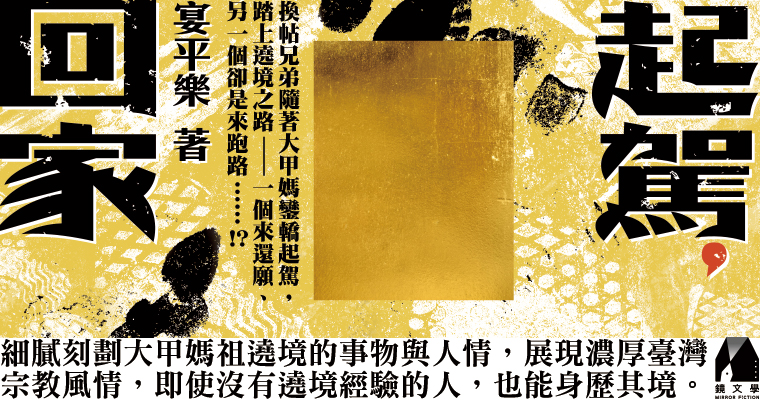那一片海,無情、且善變。
雖然孕育了萬事萬物,但是對於住在海邊的人們來說,不論多大艘的船,多有經驗的船長,一個浪頭打來說翻就翻,早上出門,下午可能就回不了家的魚寮。
生命是張狂且韌性十足的。宛如雜草般不死不休的人群,迎著黏膩的海風,對著浪濤怒吼,卻怎麼也喚不回逝去的生命。
這片海,孕育人也愁煞人。

緊鄰出海口的工廠,種了一整排木麻黃。在這靠海吃飯的魚寮邊,除了防風沙之外,隱密性也高。
然而這一天四輛進口轎車熟門熟路地開進工廠,停在門口。廠裡的老師傅、學徒,都紛紛出來探頭探腦地看著。車上下來一大票穿著黑西裝的男人。兩個穿黑衣服的年輕人蹲在門口抽菸把風,其他的魚貫進入工廠辦公室。
海風,如鐮刀般掃過,麻黃樹傳來肅殺的聲音。
有人在海上賺到錢,回家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船賣了,換成一間工廠。哪怕日子過得苦一些,至少不用早上出門,晚上等來的只剩一句口信,白髮人送黑髮人,在這裡年年復年年的上演。
工廠的辦公室裡站滿了年輕人,除了三個人坐著之外,其他人通通站著。
已經發黃的沙發上,陳肇仁泡著茶,綽號土豆的蔡正國,把手中的香菸彈進厚重的玻璃菸灰缸裡。他舉起手,旁邊的年輕人馬上將一把「貝瑞塔九○」手槍遞上。厚重且威力十足的槍枝,宛如一塊古代的驚堂木。
在這往外多跨一步就是黑水溝的地方。衝管、武士刀已經從江湖前線退下來的年代,這顆鴨頭扮演了支撐黃、賭、毒的重要權力象徵。
看到這動作,坐在對面叫做「老猴」的中年人端起桌上的茶,旁邊的年輕人馬上將手放進西裝內袋裡。
工廠裡的機器仍在運轉,金屬與金屬的碰撞聲,響徹雲霄。
辦公室裡站了超過十個大男人,然而除了熱水沸騰的聲音外,卻安靜的像午後剛睡醒的仲夏。
蔡正國把槍交給陳肇仁。
陳肇仁放下茶壺,接過槍後俐落的拉動槍機,把彈匣退出來放在桌上,並且把槍膛清空,槍口朝向自己,連同彈匣一併推給老猴。
老猴喝完茶,輕拍年輕人的手示意他後退。
「仿的?」老猴拿起槍,對了一下準星,用台語說著。
「當然嘛仿的,猴大仔,正的九○仔,一枝十八萬你買得到?」蔡正國用流利的台語回應著。
老猴點點頭,把槍放回桌上,不置可否的兩手抱胸,端詳著這枚鴨頭。
蔡正國:「猴大仔試看覓?」
老猴:「還需要試嗎?土豆大仔賣的鴨頭,甘欸臭酸?」
話一說完,老猴旁邊的年輕人將一卡皮箱推過去。蔡正國讓年輕人收下。
蔡正國:「免點看覓?」
老猴:「點啥?土豆大仔的人頭紙,甘欸減?」
老猴笑著沒回應,喝光了桌上的茶,轉身就往辦公室外走去。陳肇仁馬上站起來,跟著送到門口。工廠門口的廣場停了三輛進口轎車,後車廂敞開。
車子裡滿滿的都是槍枝,一條一條,有大有小,就像大船入港時,等著被卸貨的魚,生猛、新鮮,充滿了旺盛的生命力。
滿載而歸的人們,拿命去拚回來這些漁貨,就跟這車子裡的鴨頭一樣。工廠裡裡外外的師傅,全圍在車子旁看著這些槍。看到老猴跟陳肇仁出來,大家才作鳥獸散。
老猴滿意地坐上了車,率著眾人離去前,拍拍陳肇仁的肩膀,「你這個所在真的袂䆀。」
陳肇仁不置可否,也沒有回應,只是幫老猴將門關上。
辦公室裡,蔡正國點了三炷香插上,並且恭敬的對神壇上媽祖神像鞠躬,陳肇仁走回辦公室的時候,蔡正國將一個牛皮紙袋放在桌上。
蔡正國:「來去啊。」
陳肇仁:「稍等欸。」
蔡正國回頭看了陳肇仁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