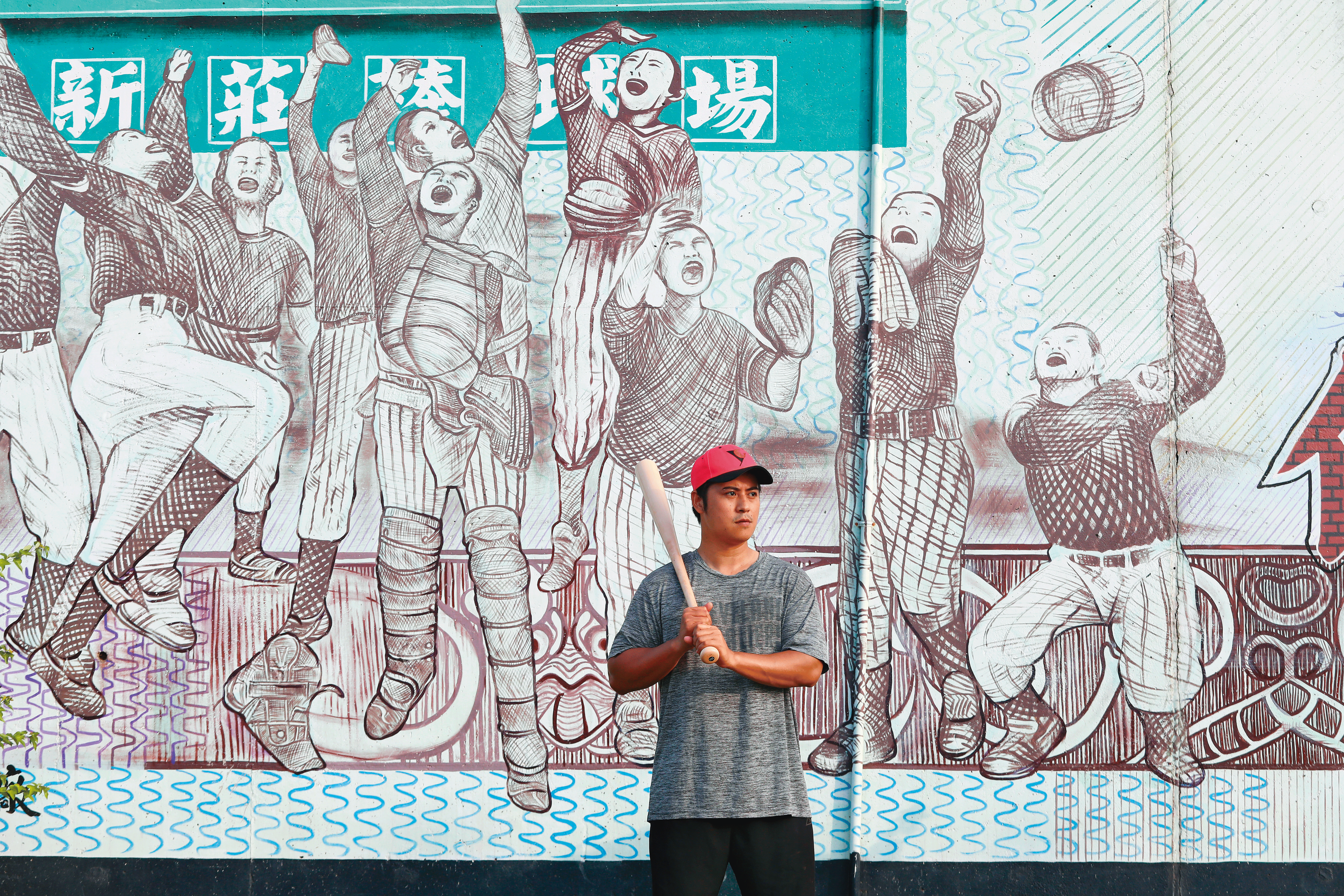比賽再過幾小時就要開始,一支甲組成棒隊正在內野場邊集合。球隊管理正和球員們交代著賽前注意事項,突然話鋒一轉,管理指著其中一位球員厲聲喝斥:「你這麼爛,幹嘛還在這裡打球?你明天不用來了。」
接著林子涵從惡夢中滿身大汗醒來。那是2018年,他因成績不理想,從崇越隼鷹棒球隊離開後的前2個月。「我被踢出球隊後,睡覺作夢都會驚醒。明天是不是要打棒球?是不是要回球隊?醒來後就哭了。我沒有球打,已經不是棒球隊的什麼了。打了十幾年球,感覺很不真實。」
常常被人說 我比不過弟弟
林子涵今年30歲,是大聯盟球星林子偉的哥哥。2018年從棒球圈離開後,他成了一名接案健身教練,亦是中華職棒成立33年來,眾多無法打進職棒的球員之一。
「2015年我要去考(職棒新人測試會)的時候,已經100多個人報名,大學我又沒拿出成績,只有一個盃賽第四名,根本沒有辦法拿出來講。」林子涵說。
林子涵大學時期棒球成績普通,守備位置主要以外野為主,偶爾兼任投手。畢業後,2015年他選擇先加入業餘甲組崇越隼鷹隊,並且轉為專職投手,球速最快仍有144公里左右。

然而2年後,林子涵卻被突如其來的壓力壓垮。2017年6月24日,弟弟林子偉升上大聯盟。「12點一過,25日是我生日,剛好新聞報導子偉上大聯盟,我覺得這是很好的生日禮物。結果朋友竟然跟我說,弟弟都上大聯盟了,哥哥怎麼在台灣?那時常常被說,我比不過弟弟,把我跟弟弟做比較,那時特別不舒服,壓力特別大。」講起這段往事,開朗的林子涵語氣突然放慢,表情有些為難,不知道該不該繼續說下去,也許是怕弟弟傷心。「我沒跟我弟講這件事。」
「說真的,國中我有點…嫉妒嗎?我有點恨我弟。」林子涵說。林子偉當初跟著林子涵腳步,加入高雄忠孝國小少棒隊,國中開始就受到外國球探注意。相較林子偉,林子涵國、高中表現就沒那麼耀眼。雖然不甘心,但對自己弟弟展現的天賦,林子涵仍然相當自豪:「我就覺得,弟弟怎麼這麼強,明明我比他早打棒球。後來覺得他真的很有天分。他跟國外球隊簽約,我當然開心,當時是沒有壓力的,開心就是開心。」

林子偉登上大聯盟後,林子涵越要求自己的表現,反而越綁手綁腳;不久後他得了投球失憶症(又名「易普症(YIPS)」,指投手完全無法控制球的走向,使投出的球完全失控的一種症狀),只能棄投從打。「大概就這樣的距離,我都會丟歪。」林子涵比了比距離,連30公尺都不到。
現在才知道 打球這麼快樂
在崇越隼鷹隊轉打者,1年後林子涵因成績不佳被球隊釋出。過了2個月的茫然期,他找了份健身教練的工作。「不能說是我弟,是我自己心理問題,我第一次來台北,第一年,到崇越都是不認識的人,給自己的壓力特別大,心理素質不夠好。」林子涵總結自己球員生涯最後所遇到的瓶頸。
一個週末,我們跟著林子涵來到大漢橋底下的河濱棒球場,看他打休閒性質的乙組成棒賽。那場比賽他守三壘,發生3次傳球失誤,但打出了帶有勝利打點的二壘安打。

比賽結束後,我問他從球員轉換其他跑道,是否遇過什麼困難?「現在覺得課業蠻重要的,尤其是英文,我還會跟我弟說:『可不可以教我英文?』一開始健身房早班外國人進來,我答不出來他要什麼,必須用手機翻譯才知道,就覺得怎麼這麼丟臉,這麼簡單都不會。」
除了外語,困擾林子涵的還有口才與社交能力。「以前的我啦,你叫我這樣跟你講話,我不可能,會緊張,然後就開始流汗。從小在球隊,因為人多,不管去哪裡都有人陪。出社會後才慢慢學會獨立,什麼都自己一個人。」
「以前是把自己束縛在一個領域,一直放不開,尤其在崇越隼鷹的時候特別嚴重。現在在乙組,才知道原來打棒球可以這麼快樂。快樂打棒球真的很舒服,工作就工作,假日可以打球,很開心,不會再想要去甲組、職棒,壓力太大。」他笑著說。
雖然接案健身教練薪水仍不算穩定,在北部生活有些吃緊,但林子涵卻仍對目前的生活方式感到自由且滿意。拍照時,為了要讓林子涵擺出投球姿勢,我充當捕手接球。林子涵半開玩笑告訴我:「很快喔,你真的可以厚?」說完後,他輕輕將球投入好球帶。
距離上職棒 只差最後一步
台灣在三級棒球(少棒、青少棒、青棒)養成過程中,球員往往需要耗費大量時間練習。雖然教育部體育署規定國中以下體育班,每日訓練時數不可超過3小時。但夜間練習及晨操,依然大量占去棒球隊學生休息時間。
除了練習,上課期間舉辦的大量棒球比賽,亦讓小球員疲於征戰。以少棒賽事為例,每年舉辦的硬式棒球盃賽,就有至少30個。「少子化後,體育班需要招生,學校會擔心拿不出成績。我可能多參加幾個盃賽,拿到前3名,就會增加曝光度與招生機會。」原住民棒球發展協會祕書長陳俊池說。
被練習與比賽占去了時間,多數小球員被訓練成眼裡只剩棒球。然而棒球在台灣作為一項職業運動,發展多年後,整體產業已經趨於完整。「我們也幫孩子開了很多課程,希望提供偏鄉體育班學生,有機會多認識整個運動產業,包含防護員、管理人員、行政人員,還有翻譯,讓他們知道可以朝整個產業發展。」陳俊池說。

但如果距離職棒只差最後一步呢?現職為怪手司機的劉展嘉,今年29歲,曾是崇越隼鷹棒球隊的外野手。「我是國體畢業的嘛,學校都有上一些心理學、生理學,教練學那些,還有運動防護。如果高中畢業就參加選秀上職棒,就學不到這些東西。」
接著劉展嘉談起自己大學球隊的學長。雖未能打進職棒,卻因習得科學訓練方式,最後成了棒球經典賽的訓練員,穿上中華隊球衣。我問他,那你當初想過多修一點其他課程,為自己在棒球外的職業鋪路嗎?劉展嘉愣了一下,回答:「其實到退伍,我的成績還是保持很好。應該可以再上去,但就是怎麼講,有時候機會問題吧。可能機會你錯過了,就什麼都沒有。」
中職歷年球隊數增減影響事件表
- 1990年:4隊/職棒元年
- 1993年:6隊/時報鷹隊、俊國熊隊加入中職。
- 1996年:7隊/和信鯨隊加入中職。
- 1997年:6隊/爆發「黑鷹事件」,1998年時報鷹解散。
- 2000年:4隊/1999年底,味全龍隊、三商虎隊解散。
- 2003年:6隊/兩聯盟合併,誠泰太陽隊、第一金剛隊加入。
- 2008年:4隊/爆發「黑米事件」,米迪亞暴龍隊、中信鯨隊解散。
青少棒國手 選秀4度失利
棒球的製作過程是這樣的:首先在軟木與橡膠的球芯外,纏上一層層羊毛線,最後再用皮革包覆,縫上108針紅線密封。那充滿縫隙的球體,久經使用後,沾上手汗、紅土、草的汁液、雨水…會散發出一股酸臭的爛皮革味。「以前撿球、整理球都會聞到,很臭。」劉展嘉說。
劉展嘉是2009年IBAF世界青少棒錦標賽國手,亦曾在職棒球員工會舉辦的青棒訓練營中,被MLB印地安人教練團,稱讚是防守好,打擊全面,極具天分的好手。他在大四時結婚生子,退伍後曾有職棒球隊向他遞出邀請,但考量當時孩子尚小,隨球隊南北奔波可能無法兼顧家庭,於是決定先進業餘隊等待機會再挑戰職棒。

2016年他加入崇越隼鷹隊,直到2019年離開成棒隊,他總共4度參加中華職棒新人測試會,3度通過測試,但皆於選秀會中落選。「第一次選是覺得最有機會,那時候在國訓隊的表現算還不錯。然後那一年沒選到,就覺得有點失落吧。只是那時候還是會想再拚個1、2年,看有沒有機會。」劉展嘉說。
和劉展嘉約訪的時間總在晚上,因為他任職的砂石場工地新開,正是忙碌的時候。這天為了拍照,晚上8點,我們將他拉到華江橋下有照明設備的棒球場。已忙碌一天的他話不多。

「剛沒球打的那3個月,天天失眠睡不著,因為我不知道我要幹嘛,不知道我能做什麼,不知道下個月有沒有收入。球隊請你離隊不會提早通知,沒個心理準備。因為我有家庭的關係,不能一直想說我還想打球。就趕快去賺錢,開始打零工。」劉展嘉染著一頭金髮,娃娃臉的他還是長得有點像學生球員,但說起家庭時表情卻相當認真。
為負擔家計 到工地做粗活
不打棒球後,劉展嘉去高爾夫球場撿過球,到中國當過業務。後來怕妻子一個人照顧孩子太累,他回到台灣當了國小女壘隊教練。但專任教練職缺少,他僅是以代課老師身分擔任助理教練,薪水一個月3萬多元,無法負擔家裡開銷。半年後,他跑去當拆除工。
「我這輩子做過最累的就是那個,就是我兩手各提30公斤,要跑1到6樓。邊抽筋邊扛,你就沒辦法放下來,怕(袋子)會破什麼的,會給人家弄花。」劉展嘉說。「我第一天真的什麼都不會,去那邊只能一直被罵。譬如說,『你以前當老師、當教練,你跑來這工地衝三小?』」
「我收入不能斷啊,只能去找這些粗活做。拆除工如果換算來說,一天二千元耶,做二十四天就有四萬八千元了。」回憶起當拆除工的日子。劉展嘉說,雖然累,但只要肯做,薪水就能負擔家計。

之後劉展嘉到砂石場當了怪手司機,目前一個月收入6萬多元,約相當於一個職棒二軍選手的薪水。「要比別人花更多的時間,更多精力,因為我什麼都不會,從一張白紙,我要把它填滿。我現在收入是比以前還要多,而且我這個是會越來越多,不會越來越少。」
只要假日不加班,劉展嘉也會打乙組成棒,他和林子涵便是同一隊隊友。問他平常已經忙成這樣,怎麼還有心力打球?「其實我覺得棒球選手,在還是球員的時候,放假聞到球皮你會想吐,味道會受不了。因為每天都在聞,每天都在打。但當你卸下選手身分,就會很懷念那個感覺,懷念那個味道。」劉展嘉說。
那麼今年中職會再新增一隊台鋼雄鷹,有想過再試試看嗎?「講難聽點,我們打棒球的,28歲就算老了。只是有時候會想說,如果再晚幾年出生,或者再早幾年出生,我現在是不是還在打球?」

從前劉展嘉是外野手,在成棒聯賽曾出現多次長傳美技。「現在沒辦法,手沒辦法,每天開怪手怎麼丟球?只能練準度了,有時候還會在場內(砂石場)拿石頭在那丟。」聽到我提起這段過去,劉展嘉笑了起來。
接著劉展嘉朝向無人的夜晚外野憑空揮臂,做出長傳的姿勢。彷彿他手中握著一顆充滿縫隙,散發出霉味的球。等球落下後,會再一次滾過紅土、草地,來到他當初守備的位置。
不顧父反對 反應快成先發
曾經獲得全壘打王的大聯盟球星Jose Bautista,在2015年於「球員論壇(The Players' Tribune)」網站上,發表過一篇,為飄洋過海來到美國打球的中南美洲球員處境發聲的文章,名為〈The Cycle〉。文章裡頭有一段寫到:「身在棒球界的我們都有一個相同的弱點:我們迷戀數字。很多人都把這群球員視為一堆小數點之後的數字,比如說,這個小伙子他對上左投的上壘率多少?他的天花板在哪裡?他會不會是下一個小葛瑞菲(Ken Griffey Jr.)?他會不會是下一個…這些球員只是孩子。」(李秉昇翻譯)
我們點開網站台灣棒球維基館,搜尋蘇志民,卻發現沒有成績數據的記載,有的只是短短幾行經歷:1983年生,174公分,80公斤。花蓮縣光復國中青少棒隊、花蓮縣國光商工青棒隊。
蘇志民是布農族人,從小被花蓮光復鄉的榮民養父收養。光復鄉孕育了許多棒球好手,包含王光輝、黃忠義、曹錦輝、周思齊…「那邊大家棒球氛圍、風氣都很好,從小我們就在路邊打棒球。」蘇志民說。
這天我們來到屏東瑪家鄉的「小農餐桌」私廚餐廳採訪蘇志民。餐廳是一間坐落在芒果園間的工寮,因為疫情並沒有對外開放,只有以麵包車與網路販售形式,銷售以原住民傳統作物製作的麵包。

見我帶來當作拍照道具的壘球棒,蘇志民和我聊起木棒的材質。我好奇問他現在還打壘球嗎?「我有打一個夜間的,晚上的球隊,我打得也不好,可是他們看到我是練家子,拿木棒然後打不到外野草皮,也不敢跟我講什麼。」蘇志民笑著說。
受到光復鄉當地棒球風氣影響,蘇志民國小三年級加入棒球隊,一開始父親反對,要他回家補習,直到五年級時,他才不顧父親反對,又再加入棒球隊。
起初他是板凳球員,1995年球隊參加全國聯賽,一次賽前,教練塞了錢給蘇志民,要他幫忙買「水果」。起初他還傻愣愣地要追上水果車,後來才想起從來沒看過教練吃水果過,這才意會到教練的意思,到檳榔攤買了檳榔。「教練說:『欸,你怎麼知道要買這個?』然後球場那時候比賽狀況是,我同學第一次執行短打的時候沒有成功,然後教練就直接叫他下來,叫我上去點,然後就成功了。」
這荒誕的劇情意外讓蘇志民成了固定先發,一直到4強賽前,蘇志民都還維持著100%打擊率。「教練跟我講,你現在就是一路殺一路打,打擊成績100%什麼的,一聽到這句話我就亂掉了。」蘇志民說。之後紀錄止步在4強賽,而當時聯賽在4強賽後才開始記錄選手個人數據,所以現在也查不到這項成績。
一度被看好 受到球探關注
國中畢業後,蘇志民和一批同樣就讀光復國小、光復國中的隊友,在教練推薦下,一起進到當時球隊剛復隊的國光商工。國光商工找來退役職棒選手王光熙當教練,因為先前球隊解散過的緣故,這批高一生成了球隊的主力球員。

賽場上,174公分、80公斤的突出身材,加上良好的打擊技巧,讓蘇志民得到了幾間大學球探的關注。「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是對穀保吧,有一顆內角球,然後我硬是把他推到反向的外野。比賽完之後,大漢、大葉大學他們,就來問一些事情。他以為我是拉打型的,說沒想到你可以打這種的球。」蘇志民說。「他們以為我高三,說畢業以後可以來。我說我才高一,他們就說:『等你畢業也可以。』」
但沒想到之後學校接連和幾位教練有了糾紛,高二下學期,球隊再度解散。「我們就被叫到教務處,教務主任跟我們說,現在球隊解散了,你們之前的住宿啊、伙食費,學雜費全部都要付,如果沒辦法付沒關係,我們學校有建教合作,你們可以去建教。」
進社會工作 體能每天下滑
因為還沒恢復原住民身分,少了學雜費減免,蘇志民成了全隊欠債最多的那個,約20萬元左右。大部分球員都選擇建教合作,到工廠上班還學校錢,而唯二能由家裡還完錢的學生,其中一個名字叫張賢智,後來打進職棒,成了誠泰Cobras隊的主力先發投手。
「我去桃園的工廠建教合作,做冷氣壓縮機的工廠。」講起這段過去,蘇志民臉上沒有太多表情:「我是靠加班才有3萬多、4萬多元,一個月還2萬元給學校,留2萬元在身上,我想要趕快出去,趕快逃。」

工作1年多後,應朋友之邀,蘇志民開始嘗試重新從乙組球隊打起。「那個時候就是,丟球都丟不出來,打擊也是球來了,都慢半拍,守備整個感覺都很差,就是怎麼會差成這樣?50公尺都丟不到,以前是隨便丟都丟得到。」蘇志民說。
「我覺得你只要開始進社會工作,你就很難再維持棒球這一塊。真的很難,因為,你每一天、每一天(體能)都在往下掉。在學生社團的時候沒有感覺,因為一直都在往上升,不會停止。可是進入社會後,比如說現在先打(球)個2天,好不容易找到手感,週休2日就結束了。你就是會一直,一直在這個狀態裡面。」
至此,蘇志民的棒球之路,在命運和生活的進逼下,算是徹底的毀了。2年半後他還完了錢,回到了花蓮。賣過羊奶,做過粗工,最後他走進餐廳,成了一名廚師。
沒留下紀錄 對球場仍憧憬
盤下第一家餐廳時,從前隊友張賢智正在職棒場上發光發熱。「只要是有他先發的比賽,我都會看完。電視其實是在廚房外面,但因為賢智比賽,我就會把它轉到廚房,變成說我在看這樣。」
問他看張賢智的比賽時,心裡頭有什麼感覺?一直沒什麼表情的蘇志民,臉上難得露出複雜又安慰的神情。「從賢智上職棒,就覺得自己同學可以打職棒,很驕傲。另外一方面,也覺得說,如果我們這些人,都還有繼續打球的話,應該會更多人上吧。我記得他新人球季就有破10勝,我覺得,他投得真的很好。」

我問他,有跟張賢智講過這些事嗎?「他不知道吧,他知道的話應該會罵我。」蘇志民有些害羞地笑了起來。這是一個沒有紀錄的球員的故事。
採訪結束後,蘇志民拍照時,他的太太目尼‧杜達利茂在一旁和我閒聊,問我怎麼會知道蘇志民打棒球的事。「他很少提自己打球的事,我都笑他是失意的棒球員。」目尼笑著說。
離開前,我問蘇志民,什麼時候會讓他最懷念打球的時光?「現在只要看到棒球場,我都會多看一眼。看到那個草皮啊,然後壘包、紅土,你都會想到很多事情。」
沒有留下紀錄的球員轉過頭,將視線移向天空,若有所思地說:「就算那裡沒有人,你都會感覺,那裡有很多事情在發生。就是有人在那邊跑步啊,訓練啊,我想的都是這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