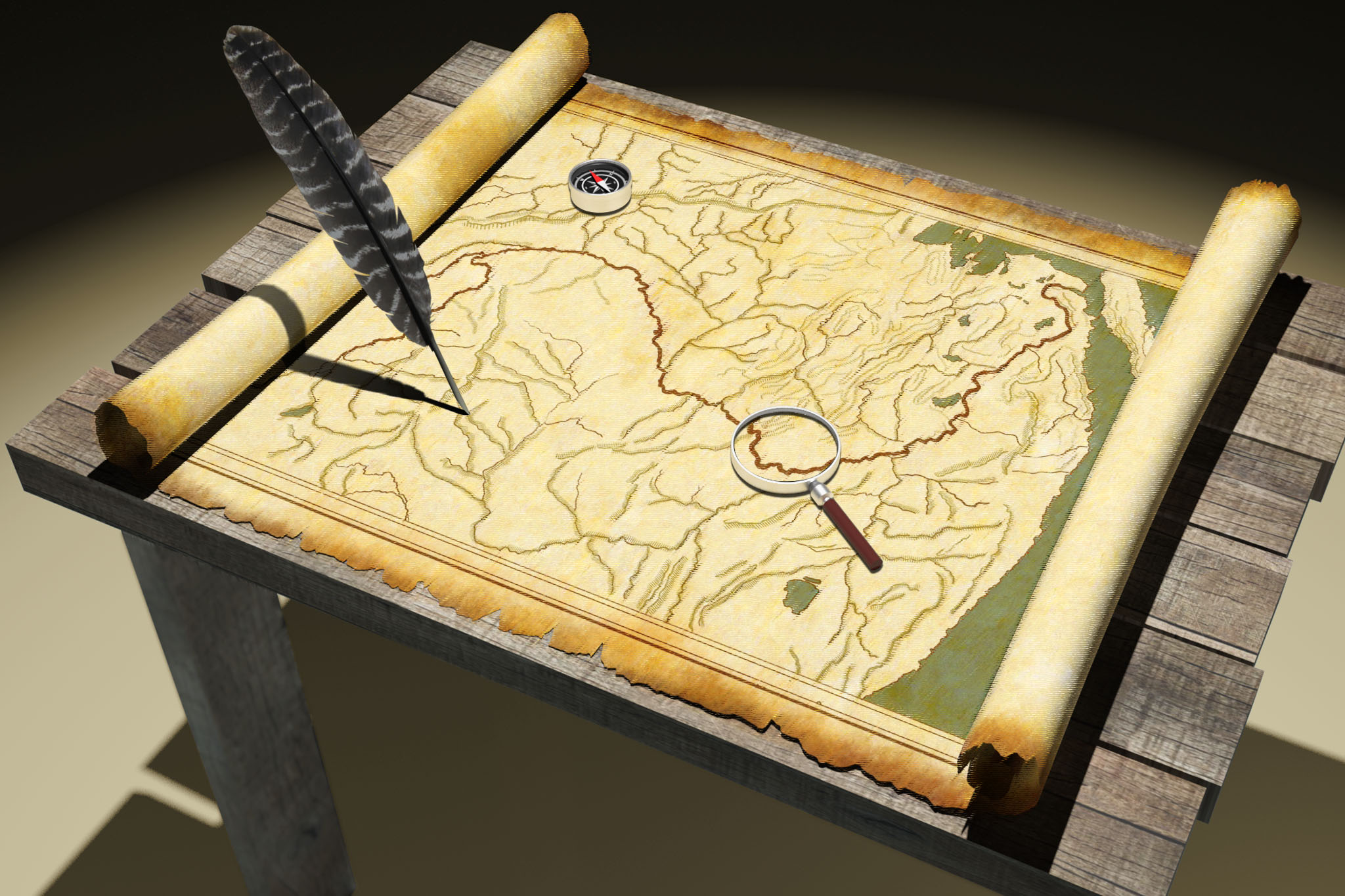廖偉棠書評〈黑龍江:遠東的死亡史──《黑龍江:尋訪帝王、戰士、探險家的歷史足跡,遊走東亞帝國邊界的神祕之河》〉全文朗讀
作為我的第三故鄉,中國東北一直是我關注的地域,無論是它的俄國殖民色彩還是它作為計劃經濟時代老工業基地的衰敗,都帶有一種蒸汽龐克式的詭異審美,同時混雜著社會學中階層研究的複雜性。因此當我看到《經濟學人》亞洲區編輯、中國通杜米尼‧齊格勒寫了本《黑龍江:尋訪帝王、戰士、探險家的歷史足跡,遊走東亞帝國邊界的神祕之河》,想當然以為是對東北黑龍江省的深度考察,馬上展讀。
歷史的沼澤會生出怪物,這怪物長得就是我們的樣子
然而並不是,《黑龍江:尋訪帝王、戰士、探險家的歷史足跡,遊走東亞帝國邊界的神祕之河》寫的是被俄羅斯人稱為阿穆爾河(Amur)的那條流經蒙古、俄羅斯與中國的大河流,寫的是從它的源頭、流域、分支、衍生等等空間變化所帶出的:遠東各民族數百年的「逐鹿莽原」,而且尤其著重於俄羅斯對遠東的「開拓」史──實際上是侵略史。

與河流的肥沃、充滿生機相對的,是人類世界的殘酷和陰慘。如果說數百頁夾敘夾議的時空穿梭行走往往給人史詩感,《黑龍江》不是一首讓人愉悅的史詩,我半個月斷斷續續的閱讀像參與了哥薩克人的冒險漂流,最終油然而生對人類的「冒險精神」、「拓荒精神」的厭惡。但同時正因為這種不適感,它成為了真正的史詩,就像不迴避黑暗的《失樂園》那樣,歷史的沼澤會生出怪物,這怪物長得就是我們的樣子。
看其英文名,也顯示了西方出版者的潛意識。這本書沒有命名為Amur River,而是掛羊頭賣狗肉一般寫了Black Dragon River──很明顯後者能給予西方讀者更多的異域想像,試想這廣告詞:「黑龍江帶你回到冒險家的時代!發現七海游俠的真相!」
《七海游俠柯爾多》(Corto Maltese)是我很喜愛的一本法國漫畫,正是它營造了我最初的遠東想像,它的動畫版《七海游俠柯爾多:西伯利亞劫金記》(Corto Maltese: La cour secrete des Arcanes)裡,「遠東」這個詞散發著紙醉金迷和生死愛慾的「性感」。這也是從18世紀以來,歐洲與俄羅斯擺脫蒙古陰影之後對一個遙不可及的法外之地的想像,《黑龍江》的前半部分描述了黑龍江的蒙古源頭與通往遠東的流程,同時也描述了俄羅斯人從恐懼到窺伺到放手擄掠的過程。
黑龍江的歷史充斥著冒險家、戰爭狂和流放者
真相是什麼呢?所謂「戰鬥民族」的俄羅斯人及其鷹犬哥薩克人,不過是亞細亞的殘暴殖民者,無異於來到美洲的白人。和某些戀殖病患者所意淫的佔有文明優勢的殖民者相反,他們是真正的蠻族,而且至今仍是,「現在無論在任何地方,有關歐洲征服與殖民新土地的陳述都不免自承罪過,或公開表示悔意。只有俄屬遠東例外。」
全書充滿對一次次攻防、屠殺的細膩描寫,血色之間交錯的是杜米尼‧齊格勒在今日遠東所見的蒼白蕭索。但相比於各路征服者以萬物為芻狗、自己也成為芻狗的荒謬劇,赤塔一章才是真正具有悲劇精神的,因為它書寫的不是製造災難的人,而是受難的人──被沙皇流放赤塔和尼布楚的十二月黨人。他們並非什麼英雄,只是覺得人之為人必須在某個歷史時刻前夕發聲,他們尋求的不是「當然」而是「應當」──後來世界上的理想主義者莫不如此。
杜米尼‧齊格勒花了很多篇幅書寫這個意象:「十二月黨人的妻子」,讓她們從我們今天習慣性用來書寫被囚禁者家眷──比如說劉霞──的修辭中還原出來,卡秋莎(十二月黨領袖楚貝茨柯王子之妻)、瑪麗亞(近衛軍少將、十二月黨人沃康斯基之妻)的形象有如莎劇中的女性一樣浮現在歷史最黯淡的時刻。她們對「罪人」丈夫的不離不棄不但是一種愛情,還是一種對信念的執著,她們把「生活」帶到了煉獄般的流放地,使革命者未遂的革命獲得了塵世的成功:流人們在尼布楚和赤塔建立起最原始的無政府主義社群。
黑龍江的歷史充斥著冒險家、戰爭狂和流放者,沒想到是最不幸的後者給予它榮光。
歌唱屠刀的最後也將引來屠刀
然而俄羅斯並不珍惜這些人,那是一個崇拜強者的民族,崇拜強者意味著自身的孱弱,這點中國和俄羅斯很像,都是外強中乾。《黑龍江》中記載的哥薩克人、布爾什維克人對原住民的屠戮,都是毫不猶豫的,只是後者打著啟蒙教化的名義。達呼爾人、鄂溫克人與南奈人、俄裔猶太人遭奴役的命運大同小異──其實俄羅斯人民又離前者有多遠呢?歌唱屠刀的最後也將引來屠刀。
2005年,總統普亭沿新修的五十八號國道重走《黑龍江》中最大的殖民者穆拉維夫從赤塔到海蘭泡這段路程,向一百五十年前順黑龍江而下的穆拉維夫致敬。差不多同時,遠東重鎮伯力推倒列寧像,卻重新樹立起穆拉維夫的雕像。這都是俄羅斯人的選擇。在《黑龍江》的末段,打著游擊隊旗號的崔亞畢辛和妮娜這兩個最後的冒險家,把尼柯萊夫斯克的白俄、日本人全部處死,只剩下「現代幻覺」和「進步」兩家劇院的廢墟,像一對隱喻,說著革命的本義就是幻覺。「城裡看不見任何紀念或譴責這場大毀滅的官式標誌」,俄羅斯的遠東夢,就這樣消亡。
那麼另一個大國呢?談論黑龍江真的能繞過中國嗎?杜米尼‧齊格勒避而不答,他的筆越接近中國越流露出疲態和矛盾,和俄羅斯人一樣。一方面,俄羅斯人視亞洲、中國人為「蠻子」(和大中華主義者對西方人的稱呼一樣),另一方面他們又被正宗歐洲人視為「東方」,以至於本國人當中的開明人士,比如說無政府主義先驅巴枯寧也反問:「整個俄羅斯帝國,不都是亞洲在統治嗎?」
他們無法處理好自己身兼東西方雙重身份這一形勢,只能一次次地對周邊生殺予奪來證明自己能左右民族的未來。而執行這一行為的人,穆拉維夫或者普亭,就成為他們的英雄。時不時像幽靈一樣出現的契訶夫、杜斯妥也夫斯基、巴枯寧等大師,都難以免俗地加入這種斯拉夫想像之中。
目睹了人類無窮無盡的殘殺與掠奪,自然天地依然包容我們存在
題為「黑龍江」卻幾乎完全不提河流南邊中國那一半,就喪失了一半追究歷史複雜性的可能,就跟周婉窈的力作《台灣歷史圖說》不提鄭成功時代一樣,殊為可惜。和中國有關的歷史描述中,至為殘忍的海蘭泡大屠殺是作者義憤難抑的一筆,最終結於博物館負責人的一句:「至於那件事,你得找專家查問了。」
杜米尼‧齊格勒諷刺著俄羅斯人的冷漠,但自己也是有選擇性地略過一些東西。

杜米尼‧齊格勒對中國的態度不無矛盾,不時刻意強調幾句如「如果不算今天的共產黨政權,滿清是中國的最後皇朝」,是他清晰的立場顯示。但唯一的一小節進入中國邊境城市黑河時,又句句都流露著中國比俄羅斯文明進步很多的觀察,揚中抑俄之筆法很明顯。關於兩國的摩擦最終以珍寶島事件告終,「突然間,黑龍江成了全世界武裝最重的邊區」,碾肉機一般的陣地易手戰過後,「士兵奉命把整件事忘了」,其實中方也一樣──尤其2005年中俄邊界東段補充協定的簽署,確定了數百萬平方公里的原清朝領土歸於俄羅斯之後。
大國一夢,從蒙古到清朝到帝俄、蘇俄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它們的爭雄野心在遠東大江大野之上顯得如此赤裸,又如此渺小。始終只有自然是這裡永恆的主人,也只有寫到物候輪換、魚躍鳥翔之時,杜米尼‧齊格勒的筆觸才分外細膩溫柔,對它們格外開恩──換句話說吧,唯其如此,我們才能感到自然天地是對人類格外開恩的,目睹了我們無窮無盡的殘殺與掠奪,依然包容我們存在;在我們製造的死亡史上,讓那些屍體成為大地的養料,堅持譜寫生命的歷史。
本文作者─廖偉棠
詩人、作家、攝影家。曾獲香港文學雙年獎,臺灣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春盞》、《櫻桃與金剛》等十餘種,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散文集《衣錦夜行》和《有情枝》, 攝影集《孤獨的中國》、《巴黎無題劇照》、《尋找倉央嘉措》,評論集《異托邦指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