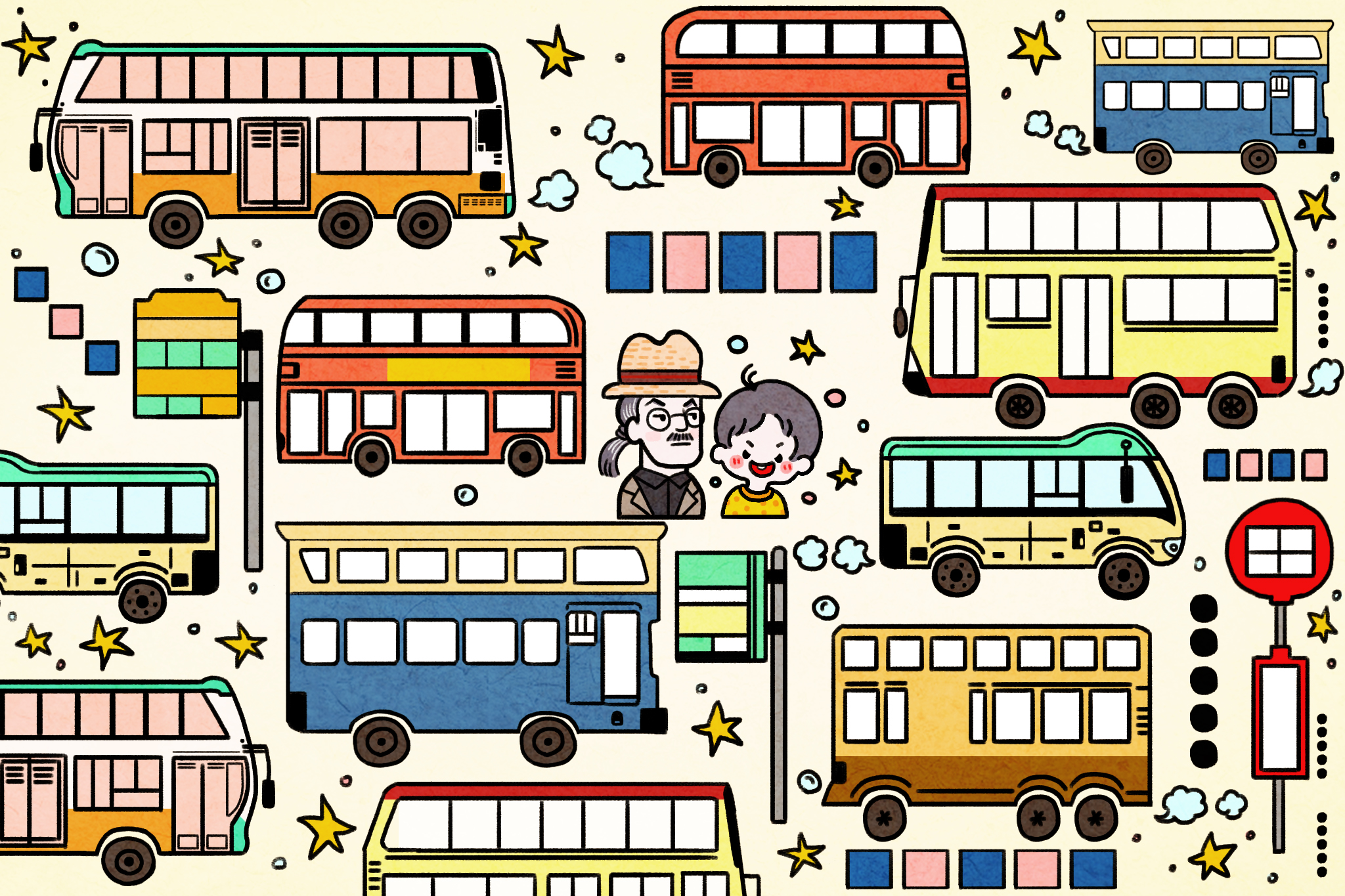廖偉棠書評〈以子之名——評董啟章《命子》〉
董啟章談《命子》成書過程和創作理念
時維立冬。閱讀香港作家董啟章新作《命子》的時候,正是香港人的兒女們紛紛受難的時候。我隨著文字上董啟章和他的兒子「果」所熱愛乘坐的一條條巴士路線,一一重訪我曾經熟悉或者依然陌生的香港地方,然而腦海中浮現的已經不是日常景象,而是這幾個月香港抗爭的現場種種。雖然,我真正的回憶應該也與董啟章一樣,是帶著我的小兒乘坐巴士,在井井有條的香港交通流轉之中,感受陽光與樹影的掠過,感謝那座城市的眷顧。
這種角力鋪墊出戀人絮語一般的文字
如此背景,很難抽離。我難以從一個香港人、董啟章的一個同行(作家、父親)的身份中抽離出一個讀者乃至批評家的身份,就像董啟章也難以從一個父親角色抽出他的作家角色——或是相反,我亦能看到從作家角色中抽出父親角色的艱難。

所以《命子》之難得,在於董啟章再度以他的清醒和筆力,把一本可能只是書寫親子關係的書,帶回到文學本體中。在三段結構的跳躍之下,我們看到董啟章與兒子的關係轉化為「作家D」與「兒子G/F」的關係,繼而帶出人類與未來的關係,靈魂與存在的關係等主題,這本書就再度進入董啟章文學世界脈絡之中,那裡面喚回「創造」本身是他始終執著的奧思。以致全書讀完,我亦能從父子、從香港的困難中凌越,直面結尾那一曲柴可夫斯基《悲慟》的蒼涼。
不過,在那麼沉重的第二、第三部份之前,我們在較為遠離虛構的、「散文」的第一部分「命子:果」裡面可以稍微閑庭信步,學習一個現實中的父親如何在焦慮中自我化解,這化解之力又多少來自一個文字中的父親。我們作為讀者曾經相信文字的治癒能力,但作為作家又如魚飲水冷暖自知,難保不自我懷疑,這種角力鋪墊出戀人絮語一般的文字——沒錯,就是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這一段「老爸維特的煩惱」,給後半部的羅蘭巴特式解構重組提供了空間。
果有超乎常孩的意志、對自己的癖好有巨大的執著
現實中董啟章的父子故事,我曾親耳聽其講述——那是屬於兩個父親之間的呻命時刻。換作文字再看,又別有一番滋味,除了能為外人道的無奈或者「荒謬」,更多的是一個父親嘗試以理性去承擔的「命」——如此看來,「命子」不只是來自陶淵明著名的「親子」詩歌的典故那層意思,更有「命中之子」、「子是吾命運」的自警。
果不是一個一般的男孩,他的種種表現甚至超出我們對「非常」男孩的想像,而在你確知他非同一般的前提下,你更難對他做出傳統意義上的「教導」——也就是董啟章流露的曾經費盡心力去做的動詞意義上的「命」。其實他與果的角力有時堪比情侶心戰,最大的挑戰在於果有超乎常孩的意志、對自己的癖好有巨大的執著。對於這種小孩,強力改造是一種辦法,但作為開明父親的董不可能如此;放棄自我投入他的興趣是一種辦法,但是作為作家的他又很難放棄自我。
有時讓人興味盎然有時頭疼的第一部分讀畢,會感覺董提供了一個關於果的詳盡檔案,如果我們參與「研究」的話,可能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果最適合的職業可能是做一個行為藝術家,以表演別的職業為業。
果自己製作自己的文集並舉辦發佈會簽售
尤其在創建「董氏企業有限公司」那一段,可以看出他強大的虛構能力(這點不得不承認是小說家的遺傳吧)、以及煞有介事地把虛構認真營造、維持的能力,其實後現代藝術裡的很多觀念藝術家、行為藝術家就是這樣行事的,這也是被我們「正常成人」貶為「孩子氣」的執著,我們又何不以審美的眼光去看、去反思他們對現實的「戲仿/諧擬」呢?
董啟章也許早就明悟了這一點,因此才能津津樂道果自己製作自己的文集並舉辦發佈會簽售一事,那裡面有果扮演「作家」職業的成份,但也真的有他寫作慾望呈現的成份。董也分別以父親和「同行」的身份去面對他,不得不承認果的文集中令父親傷心的一篇文《巴士遊河》卻是寫得最好的一篇。「⋯⋯『那時我已經忘記了父親了。』這是多麼的教人傷心的文字啊!他接著興致勃勃地描寫,坐著心愛的巴士所經過的沿路風光。去到文章末段,他終於要下車了。那個依依不捨的對象,也由從前送他上學的父親,變成今天的新型號Facelift巴士了。這就是一個父親所必須面對的命運。」憂傷之餘又何嘗沒有共鳴。
果癡迷於巴士世界的秩序,董癡迷於文學世界的紛繁——癡迷於一件事的人都是神秘主義者,就像接下來半本書裡笛卡兒癡迷於世界作為被創造物卻帶有的創造性一樣。有了前面的鋪墊,「笛卡兒的女兒」這部份就不只是一種親子關係的對應,而是一種飛躍,董之子亦人子,笛卡兒之女亦人子,當後者漸漸由幽靈變成「存在者」,前者則從實在變成文字創造之靈,也就是第三部分「命子:花」裡那個「果」的鏡像人格、再生兒「花」。
「命子:花」這一篇道盡了父親的落寞

「笛卡兒的女兒」是一個可以獨立的精彩短篇,也是董啟章的拿手好戲,來源自哲學大師笛卡兒人生一段不起眼的細節:他有一個五歲便夭折的私生女弗朗仙。董啟章發揮小說家的好事之徒本色,將之繁衍成對笛卡兒世界觀的一次考驗與提升,採取的又是「偽學術傳記」的格式,最後卻突變成賽博朋克科幻小說的場景。
笛卡兒的女兒和「花」的存在與消亡,都涉及《攻殼機動隊》的問題——也就是後者的英文名字Ghost in the Shell所包含的塞博朋克終極問題:靈魂是什麼回事?虛擬存在如何才稱得上靈魂?
董啟章有意圖探究上述問題,但他恪守了作家的本份,率先關注的應該是人情。「命子:花」這一篇道盡了父親的落寞,雖然到後面只剩下「花」的來信裡塑造的一個香港大學生的愛與死的世界,但老父之不甘仍念茲在茲。
因此到了某些細節,作家有意無意地透露著花與果之間的相似(比如說「我」給人造兒子「花」讀繪本的情節,完全重複著第一部分給果讀同樣繪本的感受),這些細節一方面讓三部分形成一個有機結構,其中笛卡兒的理論成為一個催化劑。另一方面促使讀者如果再看回去「寫實」部分的果,似乎也變得虛構化了,這本書終於成為一部小說。
我寫,故我們都在
假如我們同意父母是子女的創造者這一老話,我們就必須反思笛卡兒所說的上帝(造物主)作為第一推動力之後所需負的責、所能負的責有幾何?反之亦然,被造物又能回報幾何?「花」這一章雖然是純屬虛構,卻借這個與果迥異的「好讀書、愛文學」的兒子,替作為作家的父親說了不少話,比如說K報仇似的對作家「非本土立場」的批判,被花以沈默抵擋回去,並宣示:「世界只需要你提出簡單的答案,然後向你宣讀判決」——這一場景,相信不只是董啟章遇到過並耿耿於懷的。
悲傷的是:果與花,不相見。我們作為作家、作為父親,是因,也難以預見「果」。所以當「花」決定自己從這本書裡面抹去自己的存在的時候,我眼前浮現的卻是神秘主義版畫家埃舍爾(Maurits Cornelis Escher)的一幅名畫:一隻畫家的手在繪畫出未了的手本身。歸根到底,董啟章以這一本《命子》的寫作,奮力抵擋著虛無:無論是現實的、創造的、還是未來的虛無。我寫,故我們都在。
本文作者─廖偉棠
詩人、作家、攝影家。曾獲香港文學雙年獎,臺灣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曾出版詩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語》《春盞》《櫻桃與金剛》等十餘種,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散文集《衣錦夜行》和《有情枝》, 攝影集《孤獨的中國》《巴黎無題劇照》《尋找倉央嘉措》,評論集《異托邦指南》。